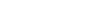何怀宏法国演讲:中国的忧伤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尊敬的南希先生、在场的女士和先生们:
我很高兴来到法国。中国深受法国文学与哲学的影响。我自己的学术研究,也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研究法国存在主义开始的,我探讨过萨特的自由哲学,还追溯到帕斯卡尔,为此还写了一本小书《生命的沉思》。我甚至还学过一阵法语,翻译过拉罗什福科的《道德箴言录》,可惜因为后来多年不用,我的那一点书面法语也差不多忘光了。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帕斯卡尔曾经说“中国晦暗不明”。我不知道这是否还是今天的状况?近百多年来中国在暗处,西方在明处,暗处对明处一般会比明处对暗处更关注,或许还能看得更清楚。但请相信我,这不是政治家的“韬光养晦”,而是实力和时势使然。
我这次讲演的主题来自我的一本书《中国的忧伤》。《中国的忧伤》是2011年6月出版的,那时中国和北京还没有出现被称之为“雾霾”的持续大规模空气污染。而有人说,这本书的封面图画已经预见了雾霾——崛起的城市高楼正罩在一片灰蒙蒙之中。那么,这也可以说是我的第一个直观的忧虑:过去常见的蓝天绿水、阳光明媚不知何时能够恢复?
请允许我还是先来简略讲一下我对中国历史的一个描述和解释,这或许能够说明我的更深层次的忧虑。三千多年前周朝的兴起,可以说使中国走向了一条世界文明国家中比较特殊的道路,它偃武修文,从信仰超越的存在转向人文实用和自身德性。作为一种我所称的“世袭社会”(HereditarySociety),它培育了一种精致的贵族文化,但对整个社会的生机和活力也有一定的压抑。但更显中国之特殊的则是两千多年前的汉制,它自建立起一个强大统一国家和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的秦朝而来,但不同于只是崇尚强力和管束性法规的秦朝,汉朝通过恢复“周文”、尊崇儒家思想和建立一种特殊的选举制度,而奠定了后来两千多年中国社会制度的基本模型,将中国从一种相对封闭的等级制社会变为相当流动的等级制社会——我将其称之为“选举社会”(Selection Society)。从汉朝到唐朝之前中国是推荐选举;从唐朝到清朝一千多年,中国则是通过诗文考试来选拔官员。官员大致总有接近乃至超过一半的人是直接来自乡村田野,来自前三代没有人做官的农民家庭,这样一种社会的垂直流动率甚至超过了现代社会的垂直流动率。中国社会还形成了一种一直延伸到民间底层的、非常重视人文教育学习啦在线学习网和文字文化的悠久传统。
中国自大规模遭遇西方,进入现代,它废除了科举制度和皇权,打破了旧有的等级结构。中国革命激烈地反传统,否定过去的主导价值和伦理规范,它试图追求国家富强和彻底的社会平等,但一度得到的却是一种一人全权统治之下的、近乎所有人的贫困的平等。到近三十多年,中国才真正走向了富强之路,但是贫富的分化也在加剧,真正民主法治的目标也还没有实现,而社会利益结构趋于固化、知识界也趋分离和分裂。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我们不宜否认新中国境内近六十五年几乎没有战争的和平——虽然前三十年还是有不断整肃的运动;更不宜否认它近三十五年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我年轻时在社会底层呆过近十年之久,做过农民、工人和士兵,尝过持续饥饿和长期失学的滋味,到三十岁才进入大学就读。我目睹了近三十多年来中国人生活明显变好、各种发展机会明显增多的过程,这是和中国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以及向世界的开放和市场经济紧密相关的。我认为:一个人的肉体生命是不能被任意剥夺和虐待的,而且必须得到符合人的身份的物质资料的供养。所以,也不能轻易否定能够保障这些基本权利的原因和条件,包括向全球开放的市场经济。如果我们不能好好对待他人的身体,也就不能好好对待自己的灵魂;而不去同情地理解千百万普通人的所欲所求,也就没有真正从内心与众人平等。
尽管不否认中国近年来取得的巨大成绩,但是,我个人还是一直比较固执地盯住中国不足的一面,让人不安和担忧的一面,尤其是在“底线生存”和“底线伦理”方面出现的危机。即在生存方面,还有一些人生活得相当艰难,还是在起码的生存线上挣扎。而如果说过去处于这种“底线生存”状态的还只是一部分人,那么,生态的危机则已经危及到所有人。过去似乎是无偿供应,人们须夷不可或缺的东西:空气、水、阳光和土壤也都出了问题,且几乎是不可逃避。而能够使我们反省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和约束伤害自然与社会的行为的社会伦理,也在根基处出现问题。传统的道德已经打破,而新的社会伦理却还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来。这些生存和道德方面的问题,我想在这次一起参与对谈的贾樟柯的《天注定》(A Touch Of Sin)的影片中已经有提炼了的、鲜明而集中的反映。但我个人虽然强烈同情、却还是不赞成一种反抗的暴力,我还是寄希望于一种经由法治和落实法治的民主。
除了这种对中国的忧伤,我或许还可说说学习啦在线学习网一种来自中国的忧伤,当然,它依然是我个人的忧虑。我并不代表什么人,但我要谈到的意见大概也反映了一个置身于现代社会的传统中国士人(读书人)的观点。中国有相当悠久的人文精英的传统,我到现在也还没有放弃这一传统,我赞成民主和平等,但对文化上还是采取一种相对保守的态度。所以,这种忧伤主要是一种对文化的忧伤。我接受却还是有些伤感中国一种精致的士人文化的衰落,包括培育了这种文化的乡村的衰落。这次与我同来的梁鸿女士,她的两本书《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就描写了这样一种乡村的衰落。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失去了故乡,我们感觉到我们原有的文化之根正在被拔起。
而这种文化的忧伤也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忧伤,也是对世界的忧伤,是对人类文化的忧伤。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的下卷结尾,试图预见现代平等社会将对人的命运、尤其是精神文化方面将产生的影响。他写道:“几乎所有的最高的东西将会逐渐下降,并为中等的东西所取代。”在这一预测接近两百年之后,我们现在或许可以来查看这一预测是否成真。文化的升降也许可以说是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情形,即在某些方面“最高的东西”下降了,而在某些方面则还有新的上升,比如在经济、科技和体育竞技等方面。但我们或许可以说这些上升的方面多是涉及到物质和身体的方面,也大多是集体累积性的结果。而下降的方面则可能是涉及到一些至关重要的方面,即一种文化中最具精神性的部分,而在这种精神性文化中,又是最具创造性的部分,亦即构成一种文化的灵魂和根本动力的东西——哲学自然是其核心的部分。还有,这些方面的下降如果的确发生了,那么究竟是何时发生的,这一下降是暂时的还是持久的,甚至是否构成了一个人类文化由上行转向下行的拐点?或者,即便下降了,是不是可以像过去的世界文明史上此伏彼起?以及,如果说有下降,甚至是根本方面的下降,那么,下降的原因是什么?它是不可避免还是可以避免的?它下降的主要原因会不会恰恰是我们赞成的、且道德上理应赞成的东西不可避免的结果?
当然,我这里仍然是一个推测,是我个人一些粗浅观察的结果。也许这整个判断就是错误的,但我的确忧虑这一可能的趋势。我把这些疑问和困惑带到法国,带给南希先生,希望得到回应。
康德在《人类历史起源臆测》的“结论”中写道:“有思想的人都感到一种忧伤,这种忧伤很有可能变成为道德的沦丧,而它又是不肯思想的人所全然不理解的:那就是对统治着世界行程的整体的天意心怀不满──当他考虑到灾难是如此沉重地压迫着人类而又(看来好像是)毫无好转的希望的时候。然而,最重要之点却在于:我们应该满足于天意(尽管天意已经就我们地上的世界为我们规划好了一条如此之艰辛的道路);部分地为的是要在艰难困苦之中不断地鼓舞勇气;部分地为的是当我们把它归咎于命运而不归咎于我们自身的时候──我们自身也许是这一切灾难的唯一的原因──使我们能着眼于自己本身,而不放过自我改进以求克服它们。”
我就以这一段话结束我的讲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