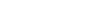开讲啦金士杰励志演讲稿:贫穷的年代 高贵的职业
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拥有这个幸运,发现自己的兴趣,然后发展它,落实它。有生之年,如果跟你的兴趣可以合二为一,我觉得那是非常幸运而且应该的。这是央视电视节目开讲啦中演讲说的一段话,欢迎查阅学习啦小编整理的开讲啦励志演讲稿。
开讲啦金士杰励志演讲稿:贫穷的年代 高贵的职业
各位同学:
大家好!我在台北曾经主持过剧团,然后也在学校教过书,带过学生,面对不少年轻人。我记得有好几次,有好几个年轻人,曾经跟我有过这样的对话,他因为马上高中毕业要考大学,或者是大学马上要毕业要进入社会,有点不知道填什么志愿,选什么行业,不知道何去何从。我说别想太复杂,你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的兴趣是什么?对不对?对方就一愣,然后陷入苦思之后回答我说,不知道。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我回到家之后我就开始很认真思考这个事,每个人不是从小到大都有些什么喜欢这个喜欢那个,有人喜欢玩一些什么花花草草,然后有人喜欢给洋娃娃穿不同的衣服,有人喜欢打鼓,有人喜欢玩汽车模型,玩飞机模型,然后有人喜欢唱歌跳舞,有人喜欢画画,这不都是兴趣嘛。按这个兴趣有一天还可以发扬光大,搞不好会变成你的工作,你的事业。我就问我自己,我的兴趣是什么?我在台北,舞台剧这个圈子里,我担任编剧,担任导演,也做演员,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兴趣。朋友还问我说,你三件事都来,你怎么形容你自己在做的事?我说我是一个说故事的人,我的兴趣就是故事这个事儿。
我现在讲我童年我觉得最最重要的一个画面,那是一个贫穷的年代,没有电视机。这个事情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整个晚上没有节目,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只剩下一件事情,就是发呆。然后有时候晚上你会看着满天的星星,看久你会发现很奇怪,你跟星星的距离会开始变,你好像觉得自己快要飞起来了,然后你会发现自己心里面出现一些声音,好像对话。“你在看我吗?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可不可以露个面出个声音让我看一看,听一听,你是谁?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站在这里是为什么?我这个人活着是为什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有一天我是不是会死?我在干什么呢?”完全的自编自导自演。这个事在当时来讲叫作穷极无聊,不过长大以后我还蛮喜欢这个动作的,我觉得生命当中必须有这个有意思的留白,它会逼使你出现一些生命当中想象不到的东西。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自言自语的方式会变,它后来会变成写日记,写信,写些杂文,或者是写些散文一些诗,其实说穿了,我是一个标标准准的文艺青年。然后这个文艺青年在十五岁的时候,他读了台湾南部的一个屏东农专畜牧兽医科。因为我想躲避大学联考,高考。因为我觉得读书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它必须是很快乐的事情,可是面对大学联考,它根本就不可能快乐,而且它很扭曲很变态,那是我主观的感受。而且我觉得我读农专,还有个好处,是那学校不会给我太大的学业压力,所以我可以利用大量的课外时间去我最爱去的地方,去书店,去电影院,最后我也这么做了。我还记得我双脚踏进书店的时候,心中的那种狂喜,我就一个字可以来形容我当时的状态,叫作“饿”,饥饿的“饿”。好像多少年我没吃一顿好东西了,现在突然把我置身这个世界级的美食餐厅,随便我吃,随便我拿,随便我用。天哪!我这手伸出去一本一本(拿)下来读的时候,我看见这手高兴得在那发抖,一本接着一本读,我在那边不能停,因为太高兴了。没有任何人逼我这么做,只有一个人逼我,就是我自己。好像我童年的时候,那些望着满天星星的那些自言自语,我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我要的答案。有一天有一本书出现了,那本书叫作《黑泽明的电影艺术》。我觉得天哪,作为一个电影导演,真的是好神圣好伟大的事情,我整个人好像被燃烧起来。是不是表示那个时候,我就心里面已经开始自我期许将来要去当一个导演,还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一个东西在跟我招手,强烈地吸引我往那个地方走。然后农专毕业了,我在养猪的牧场做事,因为我要给我爸爸妈妈一个交待。他们帮我出了钱读书,付学费,那我现在有学以致用,我没有不务正业。天天跟那个猪面对面,我记得我还经常带着一个吉他,跑到那个猪圈当中一坐,自弹自唱,因为我希望那个气氛愉快一点,那群猪就围着我转。我一手把这些猪拉扯大,从它们一出生,我帮它们接生,我帮它们剪脐带,帮它们剪牙,再大一点,我还帮它们送终,送终什么意思啊,就是送屠宰场。那个经验真不是很好的经验,因为那个方式不太人道,我当下心中有极大的难堪,我发现我只是一个商业体制底下的一个很小的生产道具,养猪这个事变得完全不浪漫。我突然对我自己说:“够了够了够了,我看猪已经看够了,我要去看人了。”
然后我就跟牧场告辞了,也是跟住在南部的父母亲告辞。我说我要去台北找工作。我的天啊,其实我根本说不清楚我要做什么,然后老人家那会还掉了眼泪。到了台北我找着工作,叫作出苦力。我为什么找出苦力的工作呢?我也是有理由的,因为我觉得我大脑非常重要,我的大脑不可以花任何力气在那些什么上班打卡,穿西装打领带吹冷气,然后打计算机画图表,我觉得太便宜了。我大脑只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读书写字创作。然后我找着的工作叫作仓库管理员,下班时间一到,我把我的纸跟笔拿出来,开始写我这一辈子第一个剧本。字斟句酌地慢慢写慢慢写,旁边那些小工在那边看电视,喝酒,打扑克牌,聊女人,我这边充耳不闻。十个月,你知道十个月有多长,跟女人怀胎一样,怀了十个月把第一个剧本写完,写完之后在最后一页写,剧终。剧本合起来,放到抽屉,关起来,这个事就完了。我没有想把这个剧本拿去给任何人看或者拿给谁发表,或者做什么其他用途,我想都没想过,我写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写它,写完了这事情就没有了,完了。
在当仓库管理员那段时间,我还常常跟朋友到台北去看一些舞台剧,那个时候台北的舞台剧叫沙漠,就是全都是一些陈腔滥调,一些教条主义,一些没有营养的东西。然后每看每骂,然后我心里想,骂干嘛呢?骂太容易了,有本事你自己干。我那个时候会做一件事,要说服人家参加我的剧团,我经常遇到一个对话,一模一样的对话,对方就望着我说:“哦哦,你要成立剧团啊,很棒很棒,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钱哪?“我就据实回答:”没有,一毛都没有。“对方就点头微笑,然后用手在肩膀上拍,一个点头。他的潜台词我完全读得懂——”理想主义,不错不错,没钱?有一天你会死得很难看。“我就不信邪,没钱就不能做演出?我告诉你,我偏偏要做这个事,我就是要一毛钱没有我还是要演给你看,天空就是我的屋顶,大地就是我的舞台,我就这么演给你看。而且我说穿了,一个人是为兴趣跑,这“跑”就不叫跑了,叫“玩”,那既然是玩,答案很清楚嘛,再苦再累再穷,都不苦不累不穷。这一帮人集合了,那是1979年的一个夏天,我站在门口,就开张之日,整个人在那边等,我一望去有来了二三十个人,陆陆续续地都来了,我看看这些人的形象怎么不太好,乱七八糟衣服,然后烂短裤,什么烂球鞋,什么拖鞋凉鞋,感觉不太像是要搞剧团,有点像是在菜市场碰到一帮人,形象不怎么良好。可是我告诉你,他们把自己白天上的班当作副业,他们把来这儿当作主业,而这个地方是零酬劳,没有名没有利,光冲这一点就知道,这一帮人不是等闲人士。他们对生活的态度,他们对生命的那种,对艺术的执着,绝不是一般人。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他们每个人心里想,我们可能要成立一个剧团了,可是我心里想,我们好像要成立一个丐帮了。然后我们给自己剧团也取了一个名字叫作“兰陵”。一年半之后,我们回到现实,我们要演出了,我们手上没有一毛钱。有一个大礼堂,搁着没用,他们提供给我们,我说好啊,不用白不用,我们就有一个场地了。没服装啊,我们每个人自己掏腰包,买了个功夫裤穿身上,因为我们剧中需要一些肢体表演。没有灯光,我们每个人从家里面搬那个爸爸妈妈打麻将的麻将灯,然后你搬一个,我搬一个,那个线不够长,再买一个延长线,这么一插,灯就亮了。然后没有宣传,我们自己打开纸,拿着笔自己画海报,画完之后再到台湾大学、师范大学门口墙上贴。没化妆没关系,素颜上去也可以演,演出那天观众席坐了二三十个人,人不多,但是其中大部分是台北文化界精英,然后我记得他们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台北市等你们这群人等了很久了,你们终于来了,你们要演下去,求求你们拜托你们,你们一定要演下去。”
好了,我不是说嘛,我们没有花什么钱,破破烂烂的条件,贫穷的剧场,我们一样演出了。但是关心的朋友不免会说好好好,你们值得鼓掌,值得加油,但是你们还是不免有三餐不济的时候,你们也总有付房租的时候,你们怎么对付?我说个事儿吧,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很有名的台湾的女作家,她叫李昂。他们家境很好,我到他们家做客,吃饭吃吃吃,我就说哇,桌上菜这么多,都好好吃啊。吃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就说,你们平常都这样吃的啊,那你们每次都吃不完,你们都怎么办呢?她说,还能怎么办呢。我说我来替你们做一下义务的食客呀什么的,她说很好,欢迎欢迎。我说别急着欢迎啊,我们可以把条件先说清楚好吗?第一,我不定时来。但是我来之前我先打电话,我说今天有没有剩饭,你说有,你说方便,方便我才来。第二,我来的时候只吃剩饭,你们家里人撤了,全部吃完了,摆的是剩饭剩菜,讲好了是剩饭剩菜,不可以因为我来你故意加一个菜,这是。必须是剩饭剩菜,她说这样子也可以啊。还有我吃这个剩饭剩菜的时候旁边不可以站着人,你旁边站个人,你跟我很客气地点头,那我就必须很客气地回以”嘿嘿嘿“这就叫社交,这叫客套,怎么样?就不专业。我要很专业地吃,没有任何多余的废话,吃完之后很干净地专业地走,说再见的时候不可以有人在那边跟我说再见,这么一社交一客套,我就觉得我下次不会来了,我就觉得心里有负担。她说好我就依着你。我也这么做了,吃了好几回,吃得好开心,觉得把我最近缺的营养都补回来了,然后我心里想,我只要有三十个这样的朋友,我一个月可以过得还蛮富足的。我还有个学生啊,结婚的时候跟我说:“老师,这么重要的日子你一定要到场。我说别了,我没有钱,我不去。”他说:“老师,不要你的钱,我要你这个人,因为这个日子对我讲意义太大了,你一定要在。“我说好好好,我们把条件说清楚啊。条件一是你要真心真意地求我,你玩假的我就不来。他说太真了,老师真的求求你来。我说好,来。”我没有红包。“”不用你的红包。“我说不给红包,但是我要打包。因为我发现酒席当中很习惯浪费很多菜,我看不过去。”没有问题,你来我帮你打包。“他说。后来他们就真的帮我打包,每次吃酒席吃了一半,我看时间差不多了,别在这混了,就想走。他们一看,金老师要走了,就开始嚷嚷,开始打包,好几个桌子一起动,塑料袋拿出来。我说慢点慢点,客人还吃一半,人家客人好尴尬。经常提一大包小包回家,好沉,但是好补。我说这些事儿,除了好玩,除了说明我的脸皮很厚以外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说明我们这种穷是完全不需要自卑的,完全不需要脸红的。甚至于反过来,我们要小心我们心里的自大,不要轻易被对方察觉。我们自大什么东西?我深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做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把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创作,拿出来给这个社会给这些人群,我们做的事情太重要了,以至于我们没有那个闲工夫赚那个闲钱。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这个穷,不是穷,是富;不是缺,是足。从某种含义来说,我们是这个城市的一种贵族。
到1980年,我们的剧团得到一个机会,参加了台北市的一个剧展,于是我们走上了正式的舞台,做正式的演出,那是第一次,简单地说吧,那天晚上一炮而红。首演那天晚上,观众在剧院里面那个欢呼声,那个鼓掌声,几乎把那个屋顶快掀掉了,好半天发现,没看见金先生,敲我的门把我拽出来,你哭什么啊?干吗呀你?我在闹情绪,我在闹别扭。我很不喜欢当下的一种感觉,一种叫成功的感觉。成什么功啊,我们庆什么功啊,你知道这个社会有时候很便宜哦,把你莫名其妙捧到一个高度,然后对着你鼓掌。“哇,你好高啊!”然后你莫名其妙就觉得自己真有那么高,我觉得那种荣耀是一种假的。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如果到学校读书,就一件事嘛,是什么?为了求知欲。与奖状无关,与你第一名我第二名,谁第三名无关,与那些通通无关,我们如果到学校读书,只有一件事会发生,就是我来读书,因为我想知道。
这两三年我在大陆跟台湾忙着演出一个舞台剧,叫作《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那是一个探讨生命和死亡的戏,相当受到好评。然后去年在上海呢,就有一个白玉兰和壹戏剧大赏同时各颁给我一个奖,记者就说:“哇,金老师你一下得的这个奖好丰收啊。”忙着追问说我得奖的感受。我还照实说了,我说,非常感激,但是坦白讲,我从小到大对奖这个东西没有任何概念和感受,没有任何想象,所以我现在有点手足无措。我觉得我这个人其实在做什么,我就好像一个长跑者,我唯一在做一件事情,我在跑,继续跑,烈日当头我在跑,跑到半道上,突然有个人跑出来:“来一杯水给你,给你喝。”我说:“哦,谢谢。”我觉得这杯水就是那个奖,我还来不及看清楚,我就把水喝了,然后说谢谢,我继续跑。
我非常高兴也非常幸运,我跑这个事情是因为我自己的兴趣而跑,它是自我的一个人生的完成。我觉得跟自己的兴趣相处,这是我的幸运。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拥有这个幸运,发现自己的兴趣,然后发展它,落实它。有生之年,如果跟你的兴趣可以合二为一,我觉得那是非常幸运而且应该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