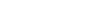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的政治经济格局
20 世纪90 年代初的中国电影生产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国家投资、以宣传为宗旨的主旋律影片,这类系列大片当时相当引人注目。第二类是艺术片,它们不如80 年代那么前卫。因数量上( 而非质量上) 的锐减逐渐成为少数派片种。第三类是娱乐片或商业片,它们题材多样,价值观各异,已经成为电影生产的主流。到了90 年代末,艺术片和娱乐影片越来越接近官方意识形态,而主旋律影片则逐渐显露出商业特征,成功吸引了一些重要的艺术影片导演,1999 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的献礼片即可作为代表。其结果是,艺术、政治和资本结成了新联盟。这是一个强大的新生力量,它重新把旺盛的创作力转向市场,也在90 年代暂时促使年轻的“地下”或“独立”导演同时在制片厂体制内外尝试电影运作。[1]
纷繁的“后社会主义”电影图景
在当前的英语学术研究中可以区分以下几种“后社会主义”观念:(1) 后社会主义作为历史分期的标签,(2) 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情感结构,(3) 后社会主义作为一系列美学实践,(4) 后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政治经济体系。毕克伟(Paul Pickowicz) 是把后社会主义与中国电影联系起来的第一位学者。他受到詹明信后现代理论的启发,推演出针对当代中国的一套类似体系。如果说“现代”指的是“在18、19 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起来的后封建的资产阶级文化”,“现代主义”指“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在西方出现的先锋……文化”,[2 ]那么,对于后毛泽东时期的中国研究来说,现代主义框架就既没有用处,也没有建设性,而只会产生误导,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社会主义中国长期使得现代主义非合法化的历史过程。出于同样原因,毕克伟从历史主义基础出发,强烈反对后现代主义框架:“后现代框架主要指后工业语境。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是以发达资本主义为前提的。”他主张不用“后现代”,而用“后社会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应物”。他认为,既然“后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为前提”,这个新框架就可以解释20 世纪80 年代的中国文化,这种文化“包含了封建帝国晚期文化的痕迹、民国时期现代文化或曰资本主义文化的残余、传统社会主义文化的残迹,也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因素”。
毕克伟把后社会主义用做一个历史分期标签,涉指“主要在晚期社会主义社会中盛行的一种负面的、反乌托邦的文化状况”。然后,他进一步把中国后社会主义定义为一种“流行的看法”,“一种异化的…… 思想和行为模式”,而它们无疑在毛泽东去世前就已出现。[3] 从这一定义看,后社会主义似乎是一种情感结构,在毛泽东时代一直被压抑,在后毛泽东时代则得到了有力表达,异化和幻灭是它的两个主题。毕克伟在研究黄建新的第一个城市三部曲时,认为《黑炮事件》(1985) 是对列宁主义政治体系的后社会主义批判,《错位》(1986)通过“戏仿”(mimicry) 将后社会主义与荒诞派戏剧联系了起来,《轮回》(1988) 则表现了后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体的听天由命和杂乱无序的状态。在另一篇文章中,毕克伟进一步用《顽主》(1988,米家山导演) 和《疯狂的代价》(1988,周晓文导演) 作为后社会主义城市电影的例证。他从改革时代电影生产的政治经济角度得出结论说,20 世纪90 年代初是一大团矛盾,此时半持政治异议的导演(如张艺谋和陈凯歌) 专门创作逆向的东方主义作品,而张元(1961 年生) 与何一(何建军,1960 年生) 等“第六代”导演则在制片厂体系外拍片,甚至还有一些与创作初衷适得其反、可能会削弱国家权力的糟糕的宣传片。[4]
毕克伟的研究表明,作为一种情感结构,后社会主义可以体现在一系列不同的电影作品中。只要它们表达了一种异化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甚至第三代名将谢晋于后毛泽东时代初期导演的电影,也可称为后社会主义。因此,后社会主义可以进一步看成各代导演采用的一套另类的美学视角。所谓“另类”,也就是与毛泽东时代主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模式不同。就城市电影而言,《本命年》(1989,谢飞导演)就先于第六代之前,描述被边缘化的出狱犯人在新兴的市场经济造成的全新的城市社区中拼命挣扎,深刻地表达了幻灭与悲观的情绪。裴开瑞(Chris Berry) 和法克哈(Mary Farquhar) 拓展了毕克伟的后社会主义观念,兼以涵盖电影风格。他们提出了以下问题:“后社会主义能否看成是后现代主义的补充? 它对其他风格的拼贴(pastiche),它的模糊性和游戏性,是否表示它的美学类似于后现代主义?”[5]换言之,我们能否按毕克伟所说,在阐释后社会主义问题时,不需面对它的他者——后现代主义?
对德里克(Arif Dirlik) 和张旭东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绝对的否定。他们认为,“我们应该记住的是,后现代也是后革命、后社会主义”。[6]他们心目中的后社会主义观念是一个新的政治经济体系,它囊括了正在变化中的社会—经济状况中所有可想象到的方面,这一状况导致了后现代在当代中国的形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张旭东在对当代中国的双重勾勒(后现代主义与后社会主义) 中,分析了极为广泛的问题。这些问题从改革的两面性、生产过剩危机、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毛泽东主义) 的乌托邦冲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市场的疯狂和平民的奢侈,到知识分子的政治焦虑(他们如今分化成几个彼此论战的意识形态阵营)。张旭东的结论是,“中国社会的经济—社会—阶级—政治—意识形态分化、矛盾、两极化、分裂化的日益深入,日益凸显,造成了焦虑”——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于是随之出现在这个可以确认为是“后社会主义的” 社会。[7]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以上我简述了近年关于后社会主义的英文学术成果,旨在说明“后社会主义”并非是涵盖整个后毛泽东时期( 即1977 年后的“新时期”) 的一个单一概念。相反,我把后社会主义看成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多样的文化图景。在这一图景下,具有不同美学追求和意识形态立场的各代影人,努力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重新调整、重新定义自己新的战略位置。我之所以强调“不同”,是因为我相信,90 年代初第六代导演出现的时期代表一个新的政治经济体系,是当代中国文化史上新的一章。这一时期有时被称为“后新时期”,它与毕克伟等研究的新时期有显著差别。[8]因此,研究20 世纪90 年代的中国电影要求我们关注新的文化生产、艺术追求、政治控制、意识形态定位以及制度变迁等问题。
新千年交替的收编和共谋
现在我们可以重新检视一下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中国电影的三股力量,重新勾勒WTO( 世界贸易组织,2001 年12 月同意中国正式加入) 时代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此,我加上了地下电影所代表的“边缘”及其自称的真实、现实,作为一个正在形成的力量,以取代前面的三分法,使描述更加精密。我们现在可以用图解的方法,把艺术、政治、资本、边缘作为四个互相竞争的力量,看一下它们相互抗衡和结合的形式( 见图)。
首先,艺术以想象为特征,由创造力产生,它追求美学、声誉,从民营企业和海外获取相当的资助,制作艺术电影,对象是国内外受过教育的小众。其二,政治的特点是权力,由审查制度维持,追求宣传和控制,利用国家拨款制作主旋律影片,以巨大的经济代价将其加诸于全国观众。其三,资本以金钱为特点,由市场推动,追求利润和控制,从民营企业——有时也有国家来源——获得大量资助,制作针对大众的娱乐片。最后,边缘以真实为特点,以异议为灵感,追求现实和声誉,从民营企业和海外获得低成本投资,制作“地下”或“独立”电影,主要在海外传播,偶尔也通过非正规渠道( 酒吧等,影碟) 在国内传播。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后的情况是,四种力量现在都把市场( 包括国内和海外市场) 作为它们的核心中国电影| 产业与叙事舞台。除了政治和边缘之间的扭结外,各种力量之间产生越来越多的融合和妥协。政治重新调整了与艺术的关系,从全面控制改为诱惑和收编。而艺术也可能会自愿融合政治,有时甚至达到了与官方意识形态完全一致的程度,如《我的1919》(1999,黄健中导演)和《国歌》(1999,吴子牛导演)。同样,资本也改变了对艺术的战略位置,从控制转向收编。有时,声誉和利润分成的诱惑推动着艺术融合资本,如《十七岁的单车》(2001,王小帅导演);或与资本共谋( 甚至依赖资本),如《英雄》(2002,张艺谋导演)。[9]艺术和边缘之间的联系是最不稳定的。从现有格局来看,艺术常常漠视边缘声称的真实,而边缘则揭示后社会主义现实中令人不快的景象,故作反抗艺术的姿态,如《小武》(1997,贾樟柯导演)。[10]有时艺术和边缘之间会出现奇特的结合或妥协,如《月蚀》(1999,王全安导演) 和《苏州河》(2000,娄烨导演),它们都类似地下电影,却公认取得了艺术成功。边缘顾名思义必须对资本表示蔑视,但在实际操作中,边缘可融合资本,而资本则部分收编了边缘,其方法是通过投资拍摄某种“中国”的现实,它被认为比艺术和政治所表现的中国现实更真实、更客观,如《邮差》(1995,何一导演) 和《站台》(2000,贾樟柯导演) 所彰示的。[11]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后,最醒目的变化出现在政治和资本的联结上。政治和资本以分享利润和资源为借口,达成了共谋关系。紫禁城影业公司就是一例,它既追求政治正确性,也追求最佳市场效应。[12]《红色恋人》(1998,叶大鹰导演) 和《不见不散》(1999,冯小刚导演) 这两部由紫禁城出品的商业片,是这种政治—资本伙伴关系的早期产物。扭结和妥协这一规则的例外情况,就是政治和边缘之间的联系,那里是可能存在政治异议和文化抵抗的唯一场所。但由于被政治禁止、被艺术忽略,边缘的影响和所呈现的现实影像主要是在海外国际电影节上被人接受,如《鬼子来了》(2000,姜文导演)。既然民营资本可以轻松吸引潜在的边缘者来搞艺术,边缘作为异议和反抗场所( 或者如白杰明所称的“寄生地”) 的未来,仍是无法确定的。[13]边缘缺乏与国内市场的结合,也使其成为新千年中国电影业政治经济中的一支弱小力量。新千年中国电影业再次被艺术、政治、资本三股力量控制,或更确切说被这三者的重新联合( 包括各自对边缘的收编) 所控制。
邓光辉在回顾20 世纪90 年代中国电影时,找出了一种合流模式,其中的“新主流电影”包括艺术片、娱乐片和新生代( 即第六代) 电影。邓光辉注意到新生代在叙述、影像风格上朝新主流运动,娱乐片则喜欢快乐原则而不是性、暴力等敏感题材,艺术片从文化批评的象牙塔沉沦到了个人幻想的后台。[14]如果重新阐释邓光辉的说法,可以说在主流的后社会主义制片模式中,收编和共谋已经是其有机成分。我对“新主流电影”这个提法有所保留,[15]但我同意邓光辉的一个论点,那就是90 年代中期以后的新变化改变了中国电影的政治经济格局。如戴锦华所说,“在80 和90 年代的社会纷乱中被放逐的边缘文化力量,现在同其他流放者一起聚集力量,开始挺进中心”。[16]戴锦华质疑两种针锋相对的未来相当令人深思:“边缘是否正在成功进军,占领中心? 还是无所不在的文化
工业及其市场策划了一场夺权? 新一代导演是给飘摇的中国电影注入了活力,还是体系淹没了软弱的个性艺术家?”[17]尽管戴锦华希望她的两种极端的未来图景都是错的,但我觉得新千年的迹象表明,后社会主义制片系统在迅速融合,电影艺术家越来越具有依赖性和共谋性,他们在相当的程度上被制度化或职业化,他们是被迫卷入而不是“挺进中心” ——而这个中心就是当今无所不在的市场。
表面看来,中国电影在WTO 时代存活下来的必要性,是最近艺术、政治、资本战略结盟后面的一个主要推动力。国家在媒体业中采取了进一步的平行、垂直整合的措施,一方面以现有的制片厂为基础,发起成立了区域性的电影集团,另一方面则把电影、电视、广播、广告、出版等整合成规模宏大的媒体集团。从制度上来说,现在的行业改组迫切要求各种力量进行更多融合和妥协。雄心勃勃的导演们则欣然抓住机会,宣布他们在市场中的存在( 虽然也许还未宣布他们自己的艺术声音)。传媒也对新一代城市导演投入了许多关注。从2002 年起,中国每年引入的好莱坞大片计划将增加两倍或三倍。在中国与好莱坞的这一新的遭遇中,新一代城市导演被看成中国的先锋。
很多新一代城市导演对WTO 时代中国电影的未来保持乐观。2000 年在回答《大众电影》杂志提出的问题时,王小帅说,好莱坞对中国艺术导演的冲击不会太大,中国电影应发展更多的“东方特色”。以地下电影《北京杂种》(1993) 著名、但已于《过年回家》(1999) 后重返“地上”的张元,把引入的好莱坞大片看成“文化的侵略和占领”,但认为年轻导演凭自己的才能和风格,会在未来十年成为最有希望的中国影人。在《头发乱了》(1994) 之后导演了《古城童话》(1999)和《西施眼》(2002) 的管虎承认,大家已达成共识,那就是电影首先必须“ 好看”,导演若不考虑市场因素就会遭到抛弃。张杨拍了两部票房成功的影片,《爱情麻辣烫》(1998) 和《洗澡》(1999),因此说得更直接:“我觉得好电影就有商业性”。[18]但是,正如真实、客观、现实、真理等概念一样,这些导演没有定义他们说的 “好电影”或“好看”是什么意思。从这个角度上说,张艺谋认为第六代的美学有泛泛之嫌,也许有一定道理:第六代“仿佛有很多不同的标准和参照物”,导致他们明显缺乏开创性的作品。[19]不少批评家也在新千年的新电影中注意到这种经典缺席的遗憾。
可以说,WTO 时代的后社会主义市场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新一代城市导演的艺术风格( 从先锋到通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俗剧式)、意识形态立场( 从激进到保守)、体裁实验( 从喜剧到犯罪恐怖片) 如此驳杂复杂。他们虽有明显缺点,但在新千年出现的新导演数量( 包括大量独立制片),以及他们某些处女作引人注目的特点,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保持乐观。引用毛泽东在“”中的语录,世界属于年轻人,虽然这一次,“世界” 不再指沉浸在政治理想主义中的红色王国,也不是被青春怒火引爆的自我放逐的个人空间,而是一个受到后社会主义电影业的力量场——资本、政治、艺术、希望还有边缘——相互作用的广阔天地。
注释:
[1]有关20 世纪90 年代中国电影的概述,见Yingjin Zhang,Chinese National Cinema. London: Routledge,2004,281-296 页.
[2] 毕克伟 (Paul Pickowicz).Huang Jianxin and the Notion of Postsocialism. Nick Browne,Paul Pickowicz, Vivian Sobchack, and Esther Yau, New Chinese Cinemas: Forms, Identities, Politics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58-59 页.
[3] 毕克伟引文同上书,60-62、80-83 页.
[4]Paul Pickowicz. Velvet Prison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Filmmaking. eborah Davis, Richard Kraus,Barry Naughton,and Elizabeth Perry,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Potential for Autonomy and Community in Post-Mao China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193-220 页.
[5] 裴开瑞 (Chris Berry) and Mary Ann Farquhar. Post-Socialist Strategies: An Analysis of Yellow Earth and Black Cannon Incident. Linda Ehrlich and David Desser,Cinematic Landscapes: Observations on the Visual Arts and Cinema of China and Japan. 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4, 84 页.
[6]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 Introduction: Postmodernism and China. Boundary 2 24.3 (1997),4 页.
[7]Xudog Zhang. Epilogue:Postmodernism and Post-Socialist Society—Historicizing the Present. 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Postmodernism and China .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 437-38 页.
[8]参见Xudong Zhang 编,Whither China? Intellectual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Durham,NC: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1 .
[9]《十七岁的单车》是一部感伤的艺术片,由台湾和法国联合制作。《英雄》是中国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影片,北京、香港和哥伦比亚亚洲公司都参与制作。
[10]张艺谋的话阐述了艺术和边缘之间的这种张力:“其他阶层的人中也存在着这种年轻的叛逆精神。第六代的反叛也是如此。我们不清楚这一反叛针对的是政治、艺术形式、艺术内容、上一代,还是传统美学。” 见Frances Gateward 编,Zhang Yimou:Interviews. 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01,153页.
[11] 在制作《站台》时,贾樟柯得到了香港胡同制作公司、日本万代娱乐公司、法国Artcam 公司的资助。比较有讽刺意味的是,张艺谋在20 世纪90 年代初从海外获得了很多资金,1999 年却抱怨年轻导演与资本的共谋“第六代很有实际考虑。这是无法抗拒的:对金钱的需求,审查制度造成的两难处境,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等等”(同上书,162 页)。
[12]我给“民营”这个词加上引号,是因为紫禁城公司在1996 年完全是国家资本建立的,投资的518 万元来自以下政府单位:北京电视台(25.5%),北京电视艺术中心(25.5%),北京电影公司 (24.5%),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24.5%)。见《1997 中国电影年鉴》 ( 北京:中国电影年鉴社,1998),第342 页. 在推出大受欢迎的“贺岁片”后,紫禁城在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成绩骄人。
[13] 白杰明 (Geremie Barmé).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39 页.
[14] 邓光辉. 论90 年代中国电影的意义生产. 当代电影,2001,1 期.
[15] 对从上海发出的“新主流电影”的提法的批评,见Yingjin Zhang,Screening China:Critical Interventions,Cinematic Reconfigurations,and the Transnational Imaginar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2002), 324-31 页.
[16] 见Jing Wang and Tani Barlow 合编, Cinema and Desire:Feminist Marx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the Work of Dai Jinhua . London:Verso,2002, 85 页.
[17] 同上书,97 页.
[18]李彦.WTO 来了我们怎么办. 大众电影. 2000,6,50-53 页.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19 ]Frances Gateward,Zhang Yimou:Interviews,16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