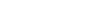中西美学中的痛苦与美:以崇高范畴为例(2)
中西美学中的痛苦与美:以崇高范畴为例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尽管中西方都有痛苦出诗人之说,痛苦产生崇高美之论,但我们仍然不难感到,中西方对痛苦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西方人对文学艺术中的痛苦有着特殊的热爱,他们认为,激烈的痛苦,令人惊心动魄的痛感,正是艺术魅力之所在,也正是崇高的真正来源。西方的宗教思想正与此一致。中国则与西方不完全一样,尽管中国也有“发愤著书”之说,“穷而后工”之论,“发狂大叫”之言,但这些并非正统理论。平和中正,“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论,才是正统的理论,什么激烈的痛苦,惊心动魄,忿愤激讦,这些都是过分的东西,都是“伤”、“淫”之属。因此,大凡哀过於伤,痛楚激讦之作,差不多都是被正统文人攻击的对象。屈原及其作品,即为突出的一例。
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原可以说是最富於悲剧性的大诗人。其作品充满了精采绝艳的崇高美。因而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所推崇者,唯屈原一人。鲁迅认为,屈赋虽然终篇缺乏“反抗挑战”之言,但其“抽写哀思,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但是这位抽写哀思、放言无惮的悲剧性诗人,遭到了后世正统文人的激烈攻击。扬雄认为,屈原内心痛苦。投江自杀是极不明智之举。他认为君子应当听天安命,不应当愤世疾俗,“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汉书·扬雄传》)班固则更激烈地抨击屈原为过激,而主张安命自守,不应露才扬己,愁神苦思,“且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志,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暨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班固认为不应当有痛苦,更不应当表现出来,甚至无论受到什么不公平遭遇也应当安之若命,不痛苦不悲伤。屈原恰恰不符合这种“无闷”、“不伤”的要求,他内心极为痛苦,作品极为放肆敢言,情感极为浓烈怨愤,於是乎班固激烈攻击道:“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若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薭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宓妃冥婚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班固《离骚序》)班固这种几乎不近人情的要求,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正统观念。这种观念对待痛苦的态度是,不应当有在过分的痛苦,因为过分的痛苦就会产生激愤怨怒之作,就会过淫、太伤,这不仅对统治不利,对“教化”不利,并且对人的身心健康也不利。《乐记》说:“ 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於身体。”中国人推崇的是抑制欲望,反情和志;不是表现极为痛苦悲惨的场面令观众惊心动魄,而是表现乎和中正,不哀不怨的内容让人心平气和,安分守己,“故曰:乐者,乐也”。所谓乐(指一种音乐、舞蹈、诗歌三合一的上古乐舞),就是让人快乐的,而不是让人痛苦的;是节制欲望的,而不是宣泄欲望的。所以说,“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反情”,孔颖达疏:“反情以和其志者,反己淫欲之情以谐和德义之志也。”即节制情感使其不过淫过伤,就能保持平和安分的状态,这样便国治家宁,身体健康了。“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乐记》)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这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正统观念,数千年来,一直被中国文人奉为金科玉律,在很大程度上,淹没了中国文学中的悲剧观念,也遏制了中国崇高观念的进一步深化。无论是令人惊心动魄、催人泪下的悲剧,还是令人恐惧痛苦的文学作品以及叫噪怒张,发狂大叫,反抗挑战的崇高,都被这抑制情感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美抹去了棱角,被拘囿於“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无形囹圄之中,而丧失了其生命的活力,最终在“温柔敦厚”的训条之中失去了力量。难怪梁启超说,中国文艺“於发扬蹈厉之气尤缺”。在“温柔敦厚”的正统观念的统治和压抑下,所有反叛的企图都不可能得逞,李贽之死就是一大明证。我们甚至还发现这样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在中国古代,不少具有崇高色彩的作家作品,都是与异端密切相关。例如:屈原的放言无惮,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建安诗人的酒笔酣歌,李白不肯摧眉折腰,李贽的发狂大叫,龚自珍的疾声高呼……尽管人们不得不承认这些作家及作品的伟大,但是在正统文人看来,这些人大多是些狂狷景行之士,所以屈原受责骂,司马迁被说成是作“谤书”,曹操为“ 雄”,李白是狂生,李贽等人,更是令正统观念所不容。至於主张痛感的崇高理论,也不被正统所容,如韩愈及其弟子的怪奇奇之论,李贽等人的流涕痛哭,欲杀欲割之说等等。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近百年来,中国学术界一直在争论,为什么中国宗教不如西方及印度发达,中国究竟有无悲剧?如有,为什么与西方的悲剧不一样?如没有,那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悲剧?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学术界。近些年来,又引起了中国有无崇高范畴之争。笔者认为,不少人在探讨这些问题时,都忘记了追寻它们的最终根源——中西方对情欲,尤其是对痛苦的不同态度。
为什么中国没有西方那种给人以毁灭感的令人惊心动魄的悲剧?最重要原因是中国文化形成的这种抑制情感的“温柔敦厚”说在起作用。西方人宁愿在艺术中描写痛苦,欣赏毁灭的痛感,而中国人却尽量避免痛苦,反对哀过於伤,更不愿看到惨不忍睹的毁灭性结局,宁愿在虚幻的美好结局之中获得平和中正的心理平衡,而不愿在激烈痛苦的宣泄之中获得由痛感带来的快感。这种不同的文学艺术传统及不同的审美心态,正是西方崇高范畴与中国温柔敦厚诗教产生的不同土壤。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文学艺术传统里具有一种偏爱痛苦的特征,因此,西方宗教特别盛行,西方将悲剧尊为文学类型之冠,将崇高视为美的最高境界。因为它们都是激烈痛苦的最高升华。与西方相反,中国文学艺术往往具有一种尽量避免激烈的痛苦,尽量逃避悲剧的倾向。因此,即便是悲剧,也要加进插科打诨,即便结局不幸,也要被一个光明的尾巴,以冲淡过於哀伤的气氛,以获得平和的心理效果。中国人也尽量讲浩然之气,阳刚之美,而不看重由痛感激起的惊惧恐怖、雄奇伟大。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古代这种克制情欲、回避痛苦、逃避悲剧的倾向,并非仅仅受儒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温柔敦厚”诗教观念的影响,而且还受到道家归真返朴,柔弱处世,乐天安命观念的影响。
当然,如果从哲学意义上讲,道家思想是充满了悲剧色彩的。老、庄都极睿智地认识到:人生即为痛苦,人生便是悲剧。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十三章)因为有身就有欲,有欲就有痛苦。有身就有死,有死就有悲哀。“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己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庄子·知北游》)这个看法与叔本华等人的观点十分近似,完全具有生命的悲剧意识了。不过面对欲望与死亡的悲剧,老、庄不是直面惨淡的人生,而是想方设法回避它。对於欲望,老子主张克制它,只要克制了欲望,知足安分,即可去悲为乐,“祸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四十六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四十四章)庄子说:“安时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庄子·大宗师》)只要安时处顺,知足长乐,欲望得不到实现的痛苦,就顿时化解了。对於死亡之悲剧,老子主张“归根复命”,这样便能长久(《老子》十六章)。庄子则主张回到大自然,与大自然同化(物化),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境界,就可以获得长生,而逃避死亡的悲剧。
老庄之种消极退避的哲学,极大地化解了中国文人的悲剧意识。因为它不像西方悲剧意识那样,积极地与可怕的大自然斗争,与可怕的命运相抗,而是回避、退让。“知其不可为而安之若命”。这种乐天安命思想,是逃避人生悲剧的最好防空洞。数千年来,多少失意文人在老庄哲学中找到了归宿,得到释平矜,逃避痛苦的慰藉。在这里,不需要将血淋淋的痛苦表现出来,而是在安之若命的训条之中淡化人生的痛苦,免去人生的悲剧。中国古代那些多得数不清的山水诗、田园诗、水墨画,就有不少属於那些逃避悲剧者的杰作。青山绿水,花香鸟语,苦杀刹清钟,白云闲鹤,在这清幽淡远的意境之中,安时处顺,与天地同乐,消尽了人间的烦恼,化解了生活之痛苦,解除了抗争之意志。这是逃避悲剧的多么美好的一处桃花源!
当然,中国古代也有以悲为美的文学艺术传统,悲秋伤时,愁绪满怀,感时叹逝,在绝大多数文人作品之中都不难找到。从宋玉的“悲哉秋之为气也!”到杜甫的“万里悲秋常做客”,从曹植的“高台多悲风”,到李白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从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到李清照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愁啊悲啊!感哟伤哟!谁说中国没有悲愁痛苦?不过,谁都不难体会出来,这种哀哀怨怨,如春江流水,似梧桐细雨般的悲愁,自然不能与西方文学中那神鹰啄食人的肝脏,儿子亲手杀死母亲那种令人恐惧的悲痛相提并论。在中国文学艺术中,悲秋感怀、伤时叹逝等淡淡的悲愁哀怨,成为了最时髦的情感。因为它符合“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要求,微微的哀,淡淡的愁,既能释躁平矜,获得心理的平衡,从而逃避人生的痛苦,又对社会无害,不会产生“乐而不为道,则乱”的效果。有时,这种淡淡的悲愁,甚至由於时髦而落了俗套,似乎谁不言愁就无诗意,不言愁就不高明。於是不少诗人作诗,往往是“为赋新诗强说愁”。这种似悲秋,如流水,如点点滴滴的黄昏雨般的悲愁,并没有成为中国雄浑范畴的内核,相反,这哀哀愁愁的悲愁,恰恰弱化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力量和气势等阳刚之美,使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美学色彩更加阴柔化,更加细腻,也更加女性化。粗犷的、野蛮的、凶猛的东西,在这里绝无市场。中国的雄浑范畴,根本不能从这种悲悲切切、凄凄惨惨之中,汲取那令人惊心动魄的,令人热血沸腾的美。这种哀哀怨怨的悲,决不是西方悲剧的悲 ,也决不是雄浑崇高的来源。而“哀而不伤”的悲,甚至有些还是无病呻吟,为文造情的悲。恰如范成大所嘲讽:“诗人多事惹闲情,闭门自造愁如许。”《石湖诗集》卷一《陆务观作〈春愁曲〉甚悲,作此反之》。
我们承认,主张抑制情感,试图逃避悲剧的儒家与道家,都产生了美的观念。但应当看到,这些观念与西方崇高美的来源是不尽相同的。认识到这一差别,才算真正认识到了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西方文化中那种强烈浓郁的宗教意识,没有出现西方式的悲剧,为什么没有出现西方那种主体与客体的强烈对抗,由恐惧痛感而产生的崇高(sublime)。更重要的是应当从这种比较之中,认识到中西方宗教与美学范畴的不同特征,承认它们各自的特色,而不是以此律彼,扬此抑彼,或用西方的标准来硬套中国的范畴;或认为中国什么东西皆古已有之,硬要将毫不相干的东西说成与西方理论一模一样。并由此进一步深思中国美学理论的价值与痼疾,探索中国古代文论走向当代审美、迈向世界文坛的广阔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