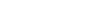刑事责任论的危局与解困(2)
时间:
刘源 赵宁1由 分享
三、刑事责任在刑法学体系中的定位
刑事责任在刑法学体系中的定位取决于其功能的确定。我国目前刑法通说将刑事责任作为“犯罪后的法律后果”,刑事责任一般被安排在犯罪论之后、刑罚论之前,形成了“罪—责—刑”的刑法体系。⒁除此之外,也有学者提出“罪—责”的刑法体系,主张犯罪是刑事责任的前提、刑事责任是犯罪的结果,刑罚、非刑罚处罚方法以及其他刑事责任实现方式都属于刑事责任范畴。⒂还有学者提出“责—罪—刑”的体系,认为刑事责任是刑法理论上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从刑事立法学的角度出发,应当是刑事责任在先而犯罪论在后。⒃
我们认为,前两种主张虽有形式上的不同,但实际上如出一辙,只不过是在关于刑罚论的认识上略有差异而已,两者都是将刑事责任理解为“犯罪的法律后果”为出发点。由于犯罪成立后必然要追究行为人法律责任这一因果关系的普遍共识,在此前提下刑事责任理论的研究就显得多此一举了,所以,尽管研究者想尽办法为刑事责任寻求独立的理论地位,但由于刑事责任理论实质内容的“空心化”,使得这些努力往往显得苍白无力。第三种观点将“责”置于“罪”和“刑(罚)”之前,以责任统领犯罪与刑罚,这是从刑事立法者的角度坚持“无责任无犯罪”的立场。但是,由于确定哪些行为构成犯罪这种立法行为本身就是对各种危害性行为进行遴选后的结果,因而犯罪本身必然表现为行为人主观上有责任且客观上实施了危害行为,因此,既然在犯罪论中已经包含了行为人责任的内容,再将责任论的内容单列且置于犯罪论之前,这样所产生的重复评价是否为学者的“益智游戏”呢?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按照将刑事责任理解为“犯罪的法律后果”的传统理论,探寻刑事责任理论在刑法体系中的地位,无异于“缘木求鱼”。刑事责任在刑法中的地位,必须建立在对刑事责任的功能进行合理解释作为出发点。如前文所述,将刑事责任功能解释为对国家刑罚权发动的合理限制,那么,刑事责任的地位就应当在犯罪论之后、刑罚论之前。也就是说,当犯罪得到确认后并且在国家刑罚权动用之前,刑事责任应当起到规制刑罚权合理发动的功能。
众所周知,刑罚权发动的前提是犯罪成立,而犯罪成立取决于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在我国刑法学体系中,犯罪构成理论是犯罪论的核心。作为一种理论学说,犯罪构成理论虽然可以在不同的学者那里自由展开和发挥,但同时它作为认定犯罪的标准或规格,在对其进行解读时必须以刑法规定为根据,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以刑法规定为依据,实际上就是要求作为理论分析工具的犯罪构成理论,在运用时必须遵循一个基本底线,即尽管简洁概括的立法语言以及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内容,都会使得对刑法规范的解释出现多种可能性,但是能够指导司法实践并为实践部门所接受的解释,必须限定在法律语言中所能包含意义的最大可解释的范围之内,不仅学理解释应当如此,而且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也必须如此,否则,就可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因此,犯罪构成理论是以文义为基础并以此展开,以形式合理性为原则,强调解释时的合规范性。既然如此,刑罚权的发动是否必然就是以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这一前提为根据或充分条件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意味着“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则刑罚权发动”的逻辑关系,那么,介乎犯罪论与刑罚论之中的刑事责任理论就缺乏了其存在所必需的独立品格。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意味着“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却并不必然导致刑罚权发动”的逻辑关系,刑事责任理论就可能成为限制刑罚权合理发动的“调节器”,同时,刑事责任理论也因为具有特定的评价范畴而具有独立品格。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性质与功能进行考察,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并非必然引起刑罚权发动。理由如下:
第一,刑罚权发动应当以行为具有实质违法性为根据。
尽管对刑罚可以给出各种不同的定义,但就刑罚是以限制或剥夺犯罪人权益为手段的法律措施,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任何异议。虽然我们可以从报应主义、功利主义或报应功利一体主义的立场,标榜刑罚是一种有效的社会制度,对刑罚权发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给予证明,但刑罚长期背负的“恶名”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作为报应的工具,刑罚显得虚伪;作为赔偿的手段,刑罚则显得无所适从;作为功利的方式,刑罚则显得残酷,且违反基本人权。⒄可见,刑罚权一旦发动,犯罪人权益必然受到侵害,从这个角度来看,刑罚是用一种“恶”实现对另一种“恶”的制裁与遏制,是一种“必要的恶”。⒅因此,刑罚惩罚的行为应当是具有危害性的行为,而不仅仅只是违反规范而实际上不具有危害性的行为。换言之,符合刑法规定(或者说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并非刑罚权发动的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
第二,刑罚权发动应当在追求普遍正义的同时,以实现个体正义为目标。
在罪刑法定原则指导下,刑罚权是否应当发动以及刑罚适用的严厉程度,都应当是以刑法规范为根据,这表明了刑罚权应以追求普遍正义为价值取向;同时,以刑法为根据对犯罪人进行惩罚,平复被害人及其亲属的情感,恢复社会秩序,这些本身又是对个体正义的实现。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普遍正义与个体正义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统一性,但是两者又并非完全一致。普遍正义是以对规则的严格遵守为前提,具有原则性;而个体正义则是以实现具体事案的公平正义为目标,具有灵活性。因此,在追求实现普遍正义时,并不必然代表着个体正义也将得以实现,甚至还可能出现为追求普遍正义,而舍弃了个体正义的情形。在我国这样一个实行单一制的国家里,各地司法机关在处理刑事案件时,必须统一遵守并执行由全国人大及其会制定的法律以及“两高”制定的司法解释,尽管存在显而易见的地域差别,但各地仍必须以这些规定为依据,这种做法很显然是以舍弃各地按照自身情况对具体事案进行处理为代价,而追求全国司法统一为目标。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就有可能出现在某些案件中如果机械地依法裁判,裁判结果可能违背常识、常理、常情的情形。比如同属于故意杀人的行为,抢劫杀人与基于义愤的“为民除害”的杀人,即使普通民众在国家依法发动刑罚权的问题上能够予以认同,但是在宣告刑罚确定问题上(不同刑罚的适用也属于国家刑罚权发动程度)通常也容易与司法机关产生很大的分歧。近年来发生的“许霆盗窃银行ATM机案”、“梁丽拾金案”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因此,刑罚权的发动应当在不违反刑法规范的前提下,着力考察具体事案中个体正义的实现。
第三,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印证了立法者意图对刑罚权发动合理性进行规制。
从刑法规定上来看,实际上立法者早已注意到刑罚权发动合理性的问题。我国刑法第63条第2款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这一特殊减轻刑罚规定正是以对具体事案特殊性的承认为前提的,实际上是通过对刑罚进行衡平,实现对国家刑罚权严厉性的限制。
综上,刑罚权发动应当以刑法明文规定为根据,坚持形式合理性的目标为前提,同时,还应当以实现具体事案的个体正义为目标,为此,刑罚适用的对象只能是那些实施了具有实质危害行为的行为人,而不能仅以行为是否违反规范作为刑罚适用的前提。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关于犯罪论和刑罚论关系的结论就是:行为符合犯罪构成,但并不必然引起刑罚权发动。换言之,在“罪—责—刑”的刑法体系中,刑事责任应当起到规制刑罚权合理发动的“调节器”的功能。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张令杰:“论刑事责任”,载《法学研究》1986年第5期;张京婴:“也论刑事责任”,载《法学研究》1987年第2期;曲新久:“刑事责任的概念及其实现”,载《政法论丛》1987年第6期;高铭暄:“论刑事责任”,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等等。
⑵杜宇:“刑事和解与传统刑事责任理论”,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1期。
⑶高永明、万国海:“刑事责任概念的清理与厘清”,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第3期。
⑷陈兴良著:《刑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53页。
⑸张明楷著:《刑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86页。
⑹张旭:“关于刑事责任的追问”,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1期。
⑺同注⑸。
⑻[日]曾根威彦著:《刑法学基础》,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
⑼王晨著:《刑事责任的一般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页。
⑽洪福增著:《刑事责任之理论》,台湾三民书局1988年版,第15页。
⑾曾粤兴、张勇:“刑罚权发动的合理性——人大代表增设拖欠工资罪议案的思考”,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⑿在保护人权成为公认的普适性价值时,自由优先于秩序就应当得到承认,但这并不等于自由是无限的、不受限制的,而是指在自由价值和秩序价值选择时,应当优先考虑自由价值的实现。
⒀[日]西园春夫著:《刑法的根基与哲学》,顾肖荣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
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18页以下。
⒂张明楷著:《刑事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页以下。
⒃王晨著:《刑事责任的一般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页以下。
⒄王水明:“论‘刑罚’恶名的由来”,载《河北法学》2007年第12期。
⒅[日]西原春夫著:《刑法的根基与哲学》,顾肖荣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