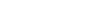浅谈元代少数民族作家杂剧创作的特征(2)
时间:
郭保红1由 分享
二、艺术特征
首先,以本色为主的语言
从语言特色的角度出发,元杂剧作家可分为三派:本色派、文采派、清丽派。关于三位少数民族作家的语言,历代评论家多有所述。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评道:“石君宝之词如罗浮梅雪”,“李直夫之词如梅边月影”,“杨景贤之词如雨中之花”。石君宝作品的语言确是朴实无华,他运用了许多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语言,以其独特的意趣,给人以通俗易懂、明白晓畅之感。因此青木正儿说:“《曲江池》和此剧(即《秋胡戏妻》)的曲辞都极有味。在本色之中,往往可以看到俊语,决非凡手所能办。《曲江池》中关于花街柳巷的话,《秋胡戏妻》中关于农家的话,在曲辞中都能巧妙的交织进去,各能灵巧地表现出他们的情趣来”。李直夫与杨景贤之词也是同样。“梅边月影”意即词风清疏素淡、朴素自然。“雨中之花”意即清丽新鲜。三人之词,准确地说是两种风格的结合。也就是说,三位少数民族作家虽有清新俏丽之词,但皆重本色,属于元杂剧作家中的本色一派,这也堪称独特。
其次,灵活多变的体制
从体制而言,元杂剧的体制通常为一本四折一楔子,在充分表达剧情矛盾冲突的发生、发展、高潮、结局的过程中,为达到完整统一,又通常以这四节奏对应四折中的每一折,但也并非所有元杂剧都尽然。
《西游记》杂剧共六本二十四折,它打破了杂剧一本四折的短小体制,成为北曲长剧的范例。当然,在杨景贤之前,打破四折一楔子的人也不是没有。据载,郑光祖的《程咬金斧劈老君堂》、张国宝的《罗李郎大闹相国寺》为四折二楔子,五折的有《元曲选》本中的纪君祥《赵氏孤儿》,但它在元刊《古今杂剧》本中仍为四折一楔子。至于六折剧本,孟称舜本《录鬼簿》中有张时起的《赛花月秋千记》和李文蔚的《金水题红怨》,但它们在天一阁本中却没有记载。因此,尚不能确定。而只有王实甫的《西厢记》以五本二十折五楔子和《西游记》构成了北曲杂剧中的两座奇峰。也就是说,继《西厢记》等剧之后,《西游记》进一步突破了元杂剧的体例限制,表达了更丰富的内容。此外,《西游记》每本前后、每折前的诗或标题在元杂剧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就音乐结构而言,唱腔上,它打破了元杂剧由正末或正旦主唱的传统,一本由多人来唱,以配合剧本的人物多、剧之淮滩贻 情长;宫调上,换宫、借宫情况较多,从而打破了一折一宫调的北曲杂剧传统,更准确地体现了人物感情的起伏变化和音乐旋律的跌宕多姿。
石君宝的剧作则在一本四折内部表现出了独特性。《秋胡戏妻》中,四折分别写了参军、逼亲、戏妻、认夫。按通 常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结构,从事件自然发展变化的 角度来谈,当发展到逼亲、迎娶,梅英必须解决矛盾时,事情已经发展到高潮,接下来就该是结局了。但事实并非如此,第三、四折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也就是说,除第一折外,其他三折皆如独幕剧,每折都有各自矛盾冲突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这样,情节的曲折变化、矛盾冲突的相互推涌,恰当地表达出了该剧的主题思想。而《曲江池》中,只有第三折如独幕剧,它通过描写李亚仙寻元和、救元和、赎自身等片断,写出了她的善良、高贵。
最后,富有民族特色的乐曲
从音乐上看,少数民族作家的剧作中采用了很多本民族乐曲。最有特色的是李直夫的《虎头牌)),如第二折[双调·五供养〕套曲中的〔阿那忽][风流体〕〔忽都白][唐兀歹7等。明代何良俊曾说:,a李直夫《虎头牌》杂剧十七换头(即〔双调·五供养」套曲)……在双调中别是一调,排名如〔阿那忽〕〔相公爱」〔也不罗」〔醉也摩擎7〔忽都白」〔唐兀歹〕之类,皆是胡语……”‘2)周德清《中原音韵》还说:“且如女真〔风流体〕等乐章,皆以女真人音声歌之。”可见,这些曲子不仅是女真族乐曲,而且最初是用女真本民族语言来演唱的。
由此可见,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从题材和艺术上都表现出了独特性。
(二)
少数民族作家能写出这样的作品绝不是偶然的,它和当时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具体来说,它与当时民族大融合的社会背景和作家的民族特质有关。
北宋以来,西、北各部少数民族迅速崛起,对处于腐朽状态的封建王朝进行了强有力的攻击。但是,面对一个文化上远远先进于自己的民族,他们在战胜之后该采取何种措施进行统治并继续生存呢?恩格斯曾经说过:“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被征服者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4)事实正是这样,金元统治者们,一方面怕被汉化,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向汉族学习。对蒙元统治者来说,他们不但建立起一套明显汉化的统治制度,而且设立了国子监学、回回国子学、蒙古子学等让各族学生学习汉文化中的传统经史。这样,正如元人戴良所说:“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兴,而西北诸国如克烈、乃蛮、也里克温、回回、吐蕃、天竺之属往往率先臣顺,奉职称蕃。其沐洪休光,沾披宠泽,与京国内臣无少异,积之日久,文轨日同,而子若孙皆亏马而事诗书。”在民族大融合背景下,一批少数民族元曲作家出现了。而就杂剧作家来说,其对汉文化的学习、运用则鲜明体现在了对前代题材的继承和发展上。
文化的影响往往是双向的,在少数民族作家受到汉文化影响的同时,他们也从其民族性出发展示了各民自族文化的独特气质、品性和风格。从前面的叙述可以得知,少数民族杂剧作家皆属本色一派,这与其民族语言密切相关。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五曾说少数民族歌曲“其言至理”,甚至连元宫廷乐舞都“撰词实腔,又皆鄙但”,这样,即使是熟谙汉文化的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时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把本民族的语言融汇进去,从而使中华民族文坛上几千年来的雅文化主流得到了一次极大的改变。这样,少数民族语言的融入,促进了元杂剧中本色一派的出现。
与先进的中原地带相比,处于落后状态的女真、蒙古等族,生活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辽阔大草原,过着逐水而居、逐草而栖的游牧生活,不停地与来自各方面的灾害做斗争,从而形成了他们尚武的习俗和粗犷、豪放、勇猛、刚毅、质朴的性格。同时,由于经济、政治等因素的相对落后,在道德文化上他们不但没有形成一套如汉民族一样对人们要求严格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礼法制度,而且还对其起到了巨大的冲击作用。这些在少数民族作家的杂剧创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不拘格套使杨景贤敢于打破旧体制,建立新体制;向往自由、追求幸福、不拘礼法使石君宝敢于提出“整顿妻纲”;而对本民族生活的热爱则使李直夫演绎了一幅声情并茂的“家乡”画面。
可见,多元因素的结合,使少数民族作家的杂剧创作呈现出了独特的风貌。这种独特,丰富繁荣了元杂剧剧坛,并为其“一代之文学”地位的确立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