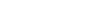浅谈古代文学审美标准对“汉赋评价”的影响
时间:
若木1由 分享
摘要 中国古代文论家对汉赋的评价颇不一致。本文试从古代文学审美批评标准入手,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以及对汉赋应采取的正确评价标准。
关键词 审美标准 汉赋 评价标准
古人对汉赋的评价颇不一致。汉代扬雄斥之为“童子雕虫篆刻”,王充非之为“虚妄之言”,唐柳冕批评汉赋“置其盛明之代,而习亡国之音”;与此相反,汉代班固赞汉赋是“雅颂之亚”,“炳焉与三代同风”。近人王国维更把它奉为“一代之文学”。为什么对同一种文学样式的评价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文艺批评标准的不同而造成的。
文艺批评标准的核心是审美标准,文学的审美批评标准是衡量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尺度。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很早就提出了真、善、美的审美批评标准。
在中国古代最早将“美”和“善”分开,并将“美”“善”标准用来评论文学艺术的是孔子,孟子继其后。孟子云:“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章句下》)这是孟子在评论人格美时说的话,后来移用于文艺。同时,庄子说的“真”和“美”也被移用于文艺。用当今的文艺观点来看,“真”是指作品的真实性,即内容能表现出客观事物自身的规律性;“善”是指作品内容的倾向性,即作品内容能表现出进步的思想倾向、正确的政治伦理观念和美好情操;“美”是指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审美性,包括艺术形象的可感性、情感性、典型性,艺术形式的完整性、多样性、独创性等等。真、善、美三者密切联系而又相互区别。对三者内涵的不同理解,对三者偏重的不同,造成古代文人对汉赋评价的不同。
一、真——作品内容的真实性
作品内容的真实性是“美”“善”的基础,没有真实也就没有“美”“善”。“真”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常用“诚”、“信”、“实”、“核”来表达,含义很广,包括言辞、事物、景象、感情的真实和艺术真实等等,如“修辞立其诚”(《易·乾·文言》),“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八十一章),“情欲信,辞欲巧”(《礼记·表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庄子·渔父》)等。王充作《论衡》,开始在文学上明确使用“真”这个概念,指出“文有真伪,元有故新”,阐明《论衡》的目的是反对“虚妄之语”,“立真伪之不平”,汉赋就是他所认为的“虚妄之语”的代表。但是,他的集焦点在于:文人史家笔下所叙述所描写的是不是符合事实,是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事件。他所说的“真”,强调的是客观事物的“真”,认为只有正确地认识、把握、再现客体的“真”才有主体的“精诚由中”,这大致是对的。但是,他还不能理解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区别。
所谓艺术真实,是指形象地反映了事务本质特征的真实,需要更多的从作品的象征意义和感情体验方面去领会真实,不能拘泥于其所言事物本身是否合乎常理。但直到南朝刘勰作《文心雕龙》才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情采》篇中指出:“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这里所说的“写真”,就是指通过景物的描写来抒发真情实感。当然,汉赋运用了大胆的想象和夸张,有诸多不符合生活真实之处,但这正是艺术真实高于生活真实之处。如司马相如《大人赋》为我们创设了一种虚无缥缈、扑朔迷离、若有若无、令人神往的神仙世界;扬雄的《甘泉赋》则提供了高度夸张、生动形象的描绘……而有些文论家,如王充等人,对这些动人的艺术描写不仅不欣赏、不认可,反而痛斥为“非”,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不能接受任何驰骋云天的想象以及与现实不符的描绘,总是以生硬死板的客观真实的标尺来衡量文学作品,对具有象征意义和夸饰性质的文艺持否定态度,结果把汉赋作品中夸张虚构的浪漫主义手法也纳入“虚妄”的范畴。这是对“真”的一种曲解。
二、善——作品内容的倾向性
作品内容的倾向性,与政治功利、道德情操密切相关。“善”是“美”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先秦时往往“美”、“善”不分。在中国美学史上,孔子首先把“善”和“美”区分开来,作为两个不同的标准来使用。如他在评论《韶》和《武》两种乐舞时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这里,“善”指思想内容而言,“美”指艺术形式而言。就思想内容来说,则有“尽善”与“未尽善”之别。因为,《韶》乐表现的是舜接受尧的“禅让”而继承王位的内容,这符合孔子的“礼让”思想,故称之为“尽善”;《武》乐表现的则是周武王以武力征讨商纣王而取天下的内容,故称之为“未尽善”。从孔子的评论来看,他对“善”的要求是很高的,“尽善尽美”的提法,应该说是美善统一,但实际上,他还是偏重于“善”。这种美善结合、以善为主导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影响深远。“善”这个功利性标准,包含着政治思想、伦理道德的内容,在中国古代常常通过与“文”相对的“道”来体现,如所谓“明道”、“载道”等,主张一切言谈论说必须合乎“道”、宣扬“道”。“道”泛指作品思想内容。但不同时代不同学派所谓的“道”,其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体现在汉赋评价中,就是强调其讽谏作用。扬雄、班固等对汉赋的评价均受孔子这一美学思想的影响。
扬雄在《法言·吾子》中说到:“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日: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批评汉赋铺陈事物、雕绘辞藻,有如学童雕琢虫书、篆写刻符,是小技末道,壮夫不为。扬雄是从儒家所强调的文学的教化作用的观点出发,认为写赋本来是要对统治者发挥讽谏、批评作用的,但是,汉赋“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的艺术形式,使它产生“劝而不止”的作用,甚至已经失去了讽谏作用。但事实上,没其讽谏之义的并不是侈丽闳衍之词,而是当时的帝王及后世的读者。文学作品是需要读者的共鸣及再创造的,如果读者不能与作者、与作品产生共鸣,不能领会其创作意图,那作品也只能被湮没。
班固认为汉赋“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着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又认为汉赋“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极力推崇这种歌功颂德的文体,并要求赋“抒下情以通讽谕”,体现的仍是儒家崇尚实际的功利主义文学观。
可见,儒家以“善”为根本、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的文学观影响着人们对汉赋的评价。
关键词 审美标准 汉赋 评价标准
古人对汉赋的评价颇不一致。汉代扬雄斥之为“童子雕虫篆刻”,王充非之为“虚妄之言”,唐柳冕批评汉赋“置其盛明之代,而习亡国之音”;与此相反,汉代班固赞汉赋是“雅颂之亚”,“炳焉与三代同风”。近人王国维更把它奉为“一代之文学”。为什么对同一种文学样式的评价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文艺批评标准的不同而造成的。
文艺批评标准的核心是审美标准,文学的审美批评标准是衡量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尺度。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很早就提出了真、善、美的审美批评标准。
在中国古代最早将“美”和“善”分开,并将“美”“善”标准用来评论文学艺术的是孔子,孟子继其后。孟子云:“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章句下》)这是孟子在评论人格美时说的话,后来移用于文艺。同时,庄子说的“真”和“美”也被移用于文艺。用当今的文艺观点来看,“真”是指作品的真实性,即内容能表现出客观事物自身的规律性;“善”是指作品内容的倾向性,即作品内容能表现出进步的思想倾向、正确的政治伦理观念和美好情操;“美”是指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审美性,包括艺术形象的可感性、情感性、典型性,艺术形式的完整性、多样性、独创性等等。真、善、美三者密切联系而又相互区别。对三者内涵的不同理解,对三者偏重的不同,造成古代文人对汉赋评价的不同。
一、真——作品内容的真实性
作品内容的真实性是“美”“善”的基础,没有真实也就没有“美”“善”。“真”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常用“诚”、“信”、“实”、“核”来表达,含义很广,包括言辞、事物、景象、感情的真实和艺术真实等等,如“修辞立其诚”(《易·乾·文言》),“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八十一章),“情欲信,辞欲巧”(《礼记·表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庄子·渔父》)等。王充作《论衡》,开始在文学上明确使用“真”这个概念,指出“文有真伪,元有故新”,阐明《论衡》的目的是反对“虚妄之语”,“立真伪之不平”,汉赋就是他所认为的“虚妄之语”的代表。但是,他的集焦点在于:文人史家笔下所叙述所描写的是不是符合事实,是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事件。他所说的“真”,强调的是客观事物的“真”,认为只有正确地认识、把握、再现客体的“真”才有主体的“精诚由中”,这大致是对的。但是,他还不能理解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区别。
所谓艺术真实,是指形象地反映了事务本质特征的真实,需要更多的从作品的象征意义和感情体验方面去领会真实,不能拘泥于其所言事物本身是否合乎常理。但直到南朝刘勰作《文心雕龙》才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情采》篇中指出:“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这里所说的“写真”,就是指通过景物的描写来抒发真情实感。当然,汉赋运用了大胆的想象和夸张,有诸多不符合生活真实之处,但这正是艺术真实高于生活真实之处。如司马相如《大人赋》为我们创设了一种虚无缥缈、扑朔迷离、若有若无、令人神往的神仙世界;扬雄的《甘泉赋》则提供了高度夸张、生动形象的描绘……而有些文论家,如王充等人,对这些动人的艺术描写不仅不欣赏、不认可,反而痛斥为“非”,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不能接受任何驰骋云天的想象以及与现实不符的描绘,总是以生硬死板的客观真实的标尺来衡量文学作品,对具有象征意义和夸饰性质的文艺持否定态度,结果把汉赋作品中夸张虚构的浪漫主义手法也纳入“虚妄”的范畴。这是对“真”的一种曲解。
二、善——作品内容的倾向性
作品内容的倾向性,与政治功利、道德情操密切相关。“善”是“美”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先秦时往往“美”、“善”不分。在中国美学史上,孔子首先把“善”和“美”区分开来,作为两个不同的标准来使用。如他在评论《韶》和《武》两种乐舞时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这里,“善”指思想内容而言,“美”指艺术形式而言。就思想内容来说,则有“尽善”与“未尽善”之别。因为,《韶》乐表现的是舜接受尧的“禅让”而继承王位的内容,这符合孔子的“礼让”思想,故称之为“尽善”;《武》乐表现的则是周武王以武力征讨商纣王而取天下的内容,故称之为“未尽善”。从孔子的评论来看,他对“善”的要求是很高的,“尽善尽美”的提法,应该说是美善统一,但实际上,他还是偏重于“善”。这种美善结合、以善为主导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影响深远。“善”这个功利性标准,包含着政治思想、伦理道德的内容,在中国古代常常通过与“文”相对的“道”来体现,如所谓“明道”、“载道”等,主张一切言谈论说必须合乎“道”、宣扬“道”。“道”泛指作品思想内容。但不同时代不同学派所谓的“道”,其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体现在汉赋评价中,就是强调其讽谏作用。扬雄、班固等对汉赋的评价均受孔子这一美学思想的影响。
扬雄在《法言·吾子》中说到:“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日: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批评汉赋铺陈事物、雕绘辞藻,有如学童雕琢虫书、篆写刻符,是小技末道,壮夫不为。扬雄是从儒家所强调的文学的教化作用的观点出发,认为写赋本来是要对统治者发挥讽谏、批评作用的,但是,汉赋“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的艺术形式,使它产生“劝而不止”的作用,甚至已经失去了讽谏作用。但事实上,没其讽谏之义的并不是侈丽闳衍之词,而是当时的帝王及后世的读者。文学作品是需要读者的共鸣及再创造的,如果读者不能与作者、与作品产生共鸣,不能领会其创作意图,那作品也只能被湮没。
班固认为汉赋“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着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又认为汉赋“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极力推崇这种歌功颂德的文体,并要求赋“抒下情以通讽谕”,体现的仍是儒家崇尚实际的功利主义文学观。
可见,儒家以“善”为根本、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的文学观影响着人们对汉赋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