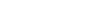试析钱锺书文学批评语体特征形成的原因(3)
时间:
焦亚东1由 分享
三、批评文体、批评对象的制约
从批评文体上看,很难想象一部用白话写就的“诗话”或“札记”是什么样子。作为中国文学批评主要的文体样式,诗话和札记自身的特点无不决定着其所使用的语言应是典雅灵动的文言语体,试简要分析之。首先,从内容上看,诗话的主要功能是点评诗作、臧否人物、追源溯流、辨彰清浊、指摘利钝以及记录诗坛轶事、诗人言行等,札记则是读书的摘要和心得,这些内容的表述,或追求的是三言两语、切中肯綮,而非宏篇大论、滔滔不绝,变为令人生畏复生厌的高头讲章,或崇尚的是魏晋以来品藻人物的清谈雅兴,讲求清新灵动、传神写意,而这些要求无疑都使文言的优势得以凸显出来,成为钱锺书考量的因素。可以说,诗话、札记的内容以及由此而决定的语言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钱锺书的语体选择。其次,从形式上讲,诗话和札记都属于笔记体,最大程度地契合了中国传统文论重视个体感悟、忽视逻辑论证的思维特点,结构松散,长短不拘,整部诗话、札记以及其中的篇章段落一般都缺少严密的理论体系、严格的范畴界定以及严谨的论证法则(始、叙、证、辩、结),在语言的要求上自然也多倾向于简练蕴藉的文言。白话尽管也可以有精炼的表述,但总体而言是无法与文言媲美的。因此,文言在语法结构和词语组合上的灵活性显然又是钱锺书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第三,从功能上看,传统文人撰写诗话的动机主要是欧阳修所说的“以资闲谈”,钱锺书在《谈艺录》“序”中所说的“托无能之词,遣有涯之日”也是此意。
札记则属于个人的读书笔记,写作目的同样带有私密的色彩。《谈艺录》、《管锥编》如果使用白话,非但不能得心应手,而且在语言形式上也显得过于庄重严肃,难免与文体的上述功能相违背,显得不伦不类。
与《谈艺录》、《管锥编》不同,在《七缀集》这类批评著述中,钱锺书则尝试使用白话进行写作,个中原因其实简单明了,因为《七缀集》采用的文体样式属于典型的西学范式,在内容上主要围绕一个明确的问题展开,在形式上不仅篇幅字数与现代学术论文没有差别,而且具有层层推演、逻辑严密的结构系统,论题的提出、概念的界定、论据的使用、论证的过程、结论的产生以及参考文献的列举,无所不包,极其规范,文言文显然难以满足这样的文体要求。文体的特点再次决定了语体的选择,同时也显示出钱锺书在文言与白话两种语体上所具有的高超的、毫无滞碍的驾驭能力。
从批评对象上看,《谈艺录》、《管锥编》论述的主要是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对于钱锺书而言,不仅要征引大量的文献资料,而且还要在随时写下自己简明扼要的评述。如果引文主要是典雅的文言,而论说又变为现代汉语,或多或少会破坏著述整体的语言风格,而且也会遇到语言和思维的转换问题。钱锺书自己也说:“因为《管锥编》里引文大都是文言文,如处处译成白话文则诸多不便亦不宜。”至于涉及到的西文与文言在语言形态上的协调问题,在钱锺书这里并未造成应有的麻烦,原因在于他的翻译已臻于“化境”,可以将西文著述译为典雅的文言。有学者指出:“钱锺书在《管锥编》内的西文雅言翻译,可以作为哪位翻译专业研究生的论文题目,尚绰绰乎有余。”钱锺书自己也说:“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到在翻译过程中尽量消除外来语言的异质性,使其在语言形态上归化于全书的语言类属和风格,是钱锺书在《谈艺录》、《管锥编》中能够使用文言的一个重要的前提,试举一例说明之:
《堂·吉诃德》第二编第五章叙夫妇絮语,第六章起曰:“从者夫妻说长道短,此际主翁家人亦正伺间进言”云云(EntantoqueSanehoPanzaYSUmujerTerseaCascajoPasaronlaimper-tinentereferidapl6tica,no estaban ociosasla sob-rinaYamadedonQuijote);《名利场》中写滑铁卢大战。结语最脍炙人口:“夜色四罩,城中之妻方祈天保夫无恙,战场上之夫仆卧。一弹穿心,死矣o”(Darknesscamedownontheif~ldandthecity:and Ameliawas prayingforGeorge,whowaslyingOilhisface,dead,with abulletthroughhisheart)。要莫古于吾三百篇《卷耳》者。男、女均出以第一人称“我”,如见肺肝而聆款唾。
颜延年《秋胡诗》第三章“嗟余怨行役”,乃秋胡口吻,而第四章“岁暮临空房”,又作秋胡妻口吻,足相参比。
这段文字节选自《管锥编》论“话分两头”叙事模式节,由于全篇的引文多为中国传统文学,所以钱锺书也使用文言翻译西方小说,而且译文只为满足说明问题之需,所以非常凝炼,仅以传达意旨为目的,这从小说中某些人物的名字被略去即可看出。如此则可避免中西引文以及钱锺书评述在语言形态上的不一致现象,无论是对于读者的阅读还是全书的整体风格都有顺畅妥帖的效果。
有学者指出:“钱先生对白话文有极深的造诣。但是在他从事学术创作时,他还是舍弃了它。考虑到钱锺书学成于五四新文化的氛围中,考虑到文言文几乎成为消亡的语言,他的举动格外耐人寻味。”事实也确实如此,赵毅衡在一篇题为《吴宓没有写出的长篇小说》的文章中曾说:“如果吴宓真能得保守真旨,见好就收,论文用文言写小说改用白话(钱锺书就是一佳例),二十年代怎么会让汪静之享情圣大名?三十年代也能给何其芳等指拨迷津,而他的长篇肯定让海伦女士比莎菲女士更享誉文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当时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前身)的《学衡》、《国风》两个刊物为阵地,形成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南高学派”(也称“东南学派”),代表人物有梅光迪、胡先辅、吴宓、柳诒徵、张其昀、缪凤林等人,他们坚守中国文化的本位立场,批评新文化运动对待传统的简单做法,被当时许多人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赵毅衡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当年的许多文化保守主义者都没能像钱锺书那样学会文化保守主义的真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真正做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多元化的价值取向,而是斤斤计较于自己在“文白之争”中的阵营和立场,所以应该写出好诗佳作的吴宓最终还是因为不能放弃对于白话的偏见,在文言与白话之间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恰当的、自由的选择,而导致计划未能演变为现实,白白丧失享誉文坛的机会。今天,再次阅读赵毅衡这段话,联想起吴宓与钱锺书这两位“亦师亦友”、学贯中西的学者在文学和学术道路上全然不同的命运,感慨良多之余,我们或许更能理解钱锺书在语言问题上的立场与态度、考量与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