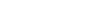中西民主制度的两次历史分野
中西民主制度的两次历史分野
摘要:中国与西方在民主制度上经历了两次历史分野。第一次分野发生在各自国家的起源时期,西方走向城邦民主制,中国走向专制集权制;第二次分野发生在近现代,西方选择三权分立体制,而中国选择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两次分野是一系列历史的和地理的原因造成的,并导致中西走上不同的政治道路。同时这两次分野也表明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符合中国现实国情和历史传统,是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民主制度;历史分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三权分立
现代政治文明的演进和传播。使民主日益成为一种神圣价值,以至于当今的任何一种政权都必须从“民主”那里取得合法性。然而,民主的神圣性并不意味着民主的现实性,民主要成为一种现实,必须依赖一种有效的民主制度的支撑。在现在的中国,这个支撑点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历史上,中西的民主制度经历了两次大分野,这是由一系列历史的和地理的原因造成的,而这两次分野的后果导致中西走上不同的政治道路。
一、第一次历史分野:城邦民主制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人类最初的社会形态是原始社会,在原始社会里,原始人对社会事务实行民主管理,这是原始民主。随着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原始民主逐渐消亡。在西方。代之而起的是城邦民主制,以古希腊城邦国家雅典最为典型;在中国,代之而起的是邦国封建制,以西周的分封制最为典型,并在秦朝发展成为专制集权制。这是中西民主制度的第一次历史分野。
城邦民主制施行于古希腊多数城邦国,以雅典最为典型,其鲜明特征有:直接民主、主权在民、轮番而治、抽签选举和多数决定等。城邦民主制极大地调动了城邦公民的政治热情和聪明才智,造就了城邦的繁荣与强盛。然而,城邦民主毕竟只是人类刚迈入文明社会时期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缺陷。例如,多数决定只片面强调多数决定,而不懂得保护少数的必要性。正是由于城邦民主制缺乏对少数利益的保护原则,没有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言论、信仰自由的观念,不少优秀的思想家、科学家如苏格拉底、普罗太戈拉等先后受到公众法庭的错误判决。这是城邦民主单纯强调多数原则所造成的悲剧。到了后来,多数原则便成了党争取的工具,给城邦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雅典之所以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败于斯巴达,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极端的多数原则造成的国内政局动荡不安和决策迟缓、失误。
邦国封建制在中国古代是一项过渡制度,主要存在于商周时期,是原始民主制向专制集权制发展的中间形态。与城邦民主制相比,它有两个显著不同的特点,一是邦国统治区域明显大于希腊城邦国,并实行等级化管理。据统计,在狭长而崎岖的古希腊半岛,共存在过近200个各自独立的城邦国,而在广阔而平坦的古中国的中原地区,周朝“先后封立了一百三十个以上(确数不可考)诸侯国”,“’到周朝后期,邦国的数量就更少了,无论是“春秋五霸”还是“战国七雄”,其国土面积都要比古希腊城邦国的霸主雅典大上几十倍、上百倍甚至更多。邦国实行等级化管理,国君、卿大夫、士、平民、奴隶是邦国的基本等级分类,依照“礼”制,等级不同,其权利与义务也不同,而且身份等级是世袭的。而雅典城邦的公民虽也有等级的区分,但经过近百年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后,所有城邦公民在政治权利上几乎是平等的了,城邦的统治者是由全体城邦公民选举产生,具有流动性。二是商周时期,“天下共主”,众邦国都源于(被分封于)一个王室,且都拥戴这个王室,这种名义上的一统为秦以后的真正大一统局面打下了历史基础。而希腊城邦各自独立发展,既不同源于一个王室或城邦,也不共同拥戴一个王室或城邦。邦国与城邦的不同,反映了古代中国与民主制的逐渐决裂,中国在向专制集权制方向发展。至秦朝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后,中国古代的政府制度始为定型,这就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专制集权制有两个主要特点:其一,君主专制,即中央的决策由皇帝个人的专断独裁,皇帝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到行使军政财政大权都具有独断性。其二,中央集权,这是针对地方分权而言,其特点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制于中央。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后果是地方和中央都必须服从皇帝一人,君主凌驾于一切之上,天下之事皆决定于君主。
中西民主制度的第一次历史分野是众多历史和地理方面的因素的综合造成的。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血缘因素和国家起源过程的特征。任何社会从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都会保留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氏族民主制。但在后来的政治发展中。西方社会以地域关系和财产关系取代了血缘关系而成为国家的结构基础。例如雅典,通过提修斯改革、梭伦改革和克里斯提尼改革最终打破了血缘关系,完成从“血族部落”到“地区部落”的转变,“居民在政治上已变为地区的简单的附属物了”。在改革的过程中,贵族和平民两大集团激烈斗争而最后达成妥协,从而形成国家基本制度和法律,这个过程的结果是原始民主制不仅没有被破坏,反而发展成为辉煌灿烂的古典民主政治。中国的早期国家也是由氏族组织转变而来的,但与西方不同的是,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氏族制的血缘关系没有受到大的破坏,中国的国家是在部族征战的过程中,战胜一方的领袖将本族的血缘关系推广并扩大,形成社会分层和国家组织,从而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血亲关系得到加强,形成强大的宗法制,从而扼杀了原始民主传统,建立了以家长统治为核心结构的王权专制制度。不像西方,这里面没有妥协,而是以彻底地征服为前提。《左传》上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是指祭祀,是提高族长的权威和维护血族团结的重要仪式,“戎”是指战争,是对异己力量的坚决镇压。宗法制和征服(而不是妥协)两个因素,使得原始民主传统在中国古代逐渐消失殆尽。
第二,地缘因素。西方政治文明发源地的希腊,地处南欧,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和小亚西亚西部海岸。境内多山,没有大河平原,交通不便,土质差,耕地有限;半岛三面临海,海岸线漫长曲折,利于海上贸易。山海的阻隔使得古希腊建立起来的国家都是城邦小国,很难有一个城邦能够完全征服其他城邦,古希腊保留城邦小国纷立的局面远较世界其它文明为长。在小国寡民的城邦里,王权“不像东方各国那样日益强大,反而逐渐衰微;绝大多数城邦终于废弃君主而实行共和;而后又限制贵族的权力,乃至在一些城邦中推翻贵族统治,建立了古代公民权利最发达的民主政治。”而中国文明发源于黄河中下游,此处多广阔平原,大河贯穿其中,沃野千里。部族之间征战不休,很容易产生彼此的兼并和征服现象,因此在中国,王权从一开始就很强大。同时,在古代中国,大江大河时常泛滥成灾,治水需要动员和组织庞大的人力和物力,以有效率的方式进行。这些如果没有强大的集权制度,这是不可能办到的。
第三,商品交换和社会结构。古希腊地理条件决定了其农业经济发展的有限性,多数城邦以工商业见长,而且许多城邦只能生产单一产品,这就决定了城邦之间在经济上必须交换沟通;同时,古希腊又拥有便利的海上运输线以及海外殖民城邦,海外贸易繁荣。这些因素使得古希腊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工商业奴隶主势力比较强大,这对希腊民主政治和文化思想都有不小的影响”。_4坍放型的商品经济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繁荣,造就了一个独立性很强的市民阶层。“国家对商品交换的介入方式是提供法律和秩序,为商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安全保障,例如罗马法就是一个系统的商业法。西方国家对商品交换的介入方式使得一个独立的市民社会能够出现在西方,这是民主制存在下去的重要条件。”而位于沃野平原中的古代中国具有发展农业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足以养活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民,因此缺乏发展商品经济的土壤。呈分散状和无组织状的数量庞大的个体农民其力量十分弱小,在强大的王权面前,他们没有力量向其要求民主权利,而只能服从既有的等级制度,不过,君王也要以“民本”道德自律,爱民,保民,恤民。国家政权重农抑商,打压商人,不给任何独立阶层成长的空间。官僚阶层之外,力量弱小又安土重迁的庞大农民是整个帝国的主体。这样的社会结构根本不是民主制度的生存土壤。
从文明演进的角度来看,中西民主制度的第一次历史分野几乎是必然的,无论是古希腊的城邦民主。还是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他们都各自适应了当时当地的历史和地理条件,是制度演进的客观结果,而不是人们主观选择的结果。两千年之后我们回顾这次历史分野的优劣得失,我们一定可以看得更清晰。就个人的自由和幸福角度来讲,民主制显然比专制集权制更富吸引力,在民主制下个人权利相对有保障,政府行为也更为透明。暴政和腐败将减少。然而,在古代社会,民主制只能施行于国事简单、人口较少的城邦小国,而不能有效管理领土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帝国。城邦小国不能保卫民主制,政治、经济和文化高度繁荣的古希腊城邦却都要无奈地亡于刚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的马其顿王国。古代强大的帝国无一不是与强大的王权和中央集权联系在一起的。专制集权制在古代社会则有利于建立、巩固和发展大一统的国家。在大一统的环境下,利于各民族的融合,也便于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得国家能有效地组织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大规模的生产和工程,大大提高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同时,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大一统在古代社会的生存能力极强。中国,无论是作为一个国家、民族,还是作为一种文化,两千多年以来,不仅一直顽强的生存下来,而且在总趋势上一直在逐渐地扩展;而西方的文化却是间断性的。“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的比较,好像两种赛跑。中国是一个人在作长时间长距离的跑。欧洲则像是一种接力跑。”在古代历史上,尽管西方不时出现灿烂文化,但该文化却不能长期生存,先进文化不时被落后文化所吞并,古希腊亡于马其顿王国,罗马亡于北方蛮族;中国的王朝虽然也常被落后民族所取代。但在文化上。没有任何一个外族文化能够将中国文化吞并。尽管这不全是专制集权制的功劳,但是专制集权制在捍卫种族生存空间和文化上,的确起着重大的作用。然而,专制集权制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是暴政和腐败现象屡屡出现:其次是等级森严,社会禁锢很多,个人缺乏自由;再次,社会结构高度同质化,不利先进技术和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