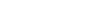有关老屋的抒情散文:隐进岁月深处的老屋
学习啦:老屋总是承载着一段记忆,一段回不去的岁月。下面让我们一起来阅读《隐进岁月深处的老屋》这篇文章吧!
打开锈迹斑斑的铁锁,推开紧闭在记忆里的大门,站在熟悉而寂静的院子里,荒芜之感在我心里放肆的蔓延:触目所及,院子里,台阶的缝隙间,乃至高高的墙头上,荒草侵占了没有被水泥地封严实的每一寸土,寒风中傲慢冷峻的耸立,一阵风过,草尖轻摇,俨然在向我这个院落的主人宣告着它的不可侵犯。
这哪里是我魂牵梦绕的家?哪里是我记忆中的老屋?哪里是父亲半世心血铸就的华堂?
几回回梦里回故园,依旧是一颦一笑一宛然。曾经在这里呼吸着一家人呼吸的空气,踩着院子里一家人叠了无数摞的脚印,每一个角落都在我记忆里重重叠叠,鲜活如昔。那些岁月,似永恒的梵音,在我头顶轰然作响,在我耳畔绵绵不绝。似一团火一片光,席卷着、漫延着、灼烧着我沉痛的心。
恍惚间,那些握不住的如烟过往,好像才走过短短的一日,又好像已沉埋漫长的千年……
这个院落的房屋曾几度变迁,承载着父母一生的辛勤劳作,承载着我们成长历程中所有的喜怒哀乐,承载着我们幸福一家人的浓浓亲情。
记忆中最早的老屋是三间“瓦接檐”,那已经是村子里通体气派的房子了。但是从姥姥给我絮絮叨叨过无数次的对爸爸当年情景的“讨伐”翻唱中,母亲刚嫁给父亲的时候,父亲应该是仅有一间小小的茅草屋的赤贫小子。刚做新娘三天的母亲在茅草屋里,费力的点燃着湿漉漉的柴草,浓烟充斥了小草屋,烟熏火燎中,母亲正被呛得咳嗽不止,眼泪汪汪的时候,来接母亲回门的姥姥刚好出现在门口。姥姥在屋子里搜罗一遍,只看到一张破床,两只旧碗,一个小铁锅,连筷子都是柴草棍折成的,难过得话都说不出来了:她的幺女就因为家里成分不好,被连哄带骗的嫁给了这么个家徒四壁的“贫农”!还有四天就过年了,看着这个连年货都没有置备的“家”,姥姥果断破除出嫁的闺女不能在娘家过年的旧俗,指挥着父母,收拾了简单的包裹,相跟着去她家过年了。从小缺失母爱的父亲,从此每到新年,都在姥姥家安享热气腾腾的升起来的阖家团圆的温馨……母亲从没有跟我们讲过这一段囊中如何羞涩,日子如何艰难,也许那时年轻的父母希望满满,即使每天为一碗羹汤裹腹而绞尽脑汁也不觉得苦吧。
父母是如何从那个四壁皆空的茅草屋里起步,开始为最基本的安居而打拼的,我不得而知。从记忆时起,我们家就一直在房屋变迁的种种过渡中东挪西迁,在这个不大的院落里候鸟一样迁徙“流浪”。
十一岁就独自带着年幼的四叔出来闯荡的父亲,为了生存,百艺皆通,是村里的能工巧匠。当时,泥瓦匠是乡村里的“高级工程师”,父亲就是高工之首。这一桂冠,我猜,一定是父亲一次又一次的盖房中磨练出来的。抱有给我们一个高大上的安乐窝的鸿鹄之志的父亲,从结婚时房屋无片瓦的一间茅草屋,到先是两间后又扩展到三间的瓦接檐,到村子里第一栋大瓦房(用栋才可以表现它的气派,大瓦是区别于当时大家看不上但现在是稀有物种的小青瓦),一直折腾到村子里第一栋四间高大宽敞的平房。父母大半生的精力,除了抚养我们,都源源不断的倾注在一波又一波的建新房上了。
在那衣仅蔽体食仅裹腹的年代,房子是最大的奢侈品,更是衡量一个家庭是否富足的不二标签。每一步艰难的换房之旅之后,父亲都像骄傲的孔雀般睥睨众小,在众人钦佩崇拜的眼神聚焦中容光焕发。
趁着农活之余的黄昏拂晓,父亲就到附近的山上,或炸药炸,或撬杠撬,或大锤抡,把硕大无比的石头从山体里炸出来,砸成需要的大小样式,一块一块的搬到车上,再从蜿蜒崎岖的山道上,一车车历尽千辛万苦拉回来。我和妹妹寒假也会跟着上山帮忙搬石头,一趟下来,已是手破脚软,棉袄汗湿,山风一吹,热气腾腾的汗顿时冷如冰,附在身上,冻得寒颤都打不出来。而父亲在呼出的团团白雾中,一声仰天长啸,大锤子一抡,巨人样的石头四分五裂,飞沙走石,石末乱溅。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石头运下山后,那些棱角分明,品貌俱佳的,卖给县城里的建筑队,其余的就是父亲新房的坚实地基,或院子里打地平的原材料了,石头和着父母的汗水堆满了院子,父亲漫长的建房之旅又拉开了序幕。因为要在原地建新房打地基,主房就要扒掉,我们只好栖身于逼仄的厨房里,而厨房,则委屈到旁边的临时棚子里。连绵不断的雨天,从四处漏风头上漏雨的棚子里到厨房里,到处是黏糊糊湿漉漉的,瑟瑟发抖中躲进被窝里,被褥湿冷似铁。我们姊妹几个对于住进宽敞明亮不漏雨的大房子的期盼,每到雨季就如雨后春笋般疯涨着。
终于,石头换成了一沓沓的纸币,盖房的红砖拉回来了,铸顶的水泥钢筋预制板拉回来了,水泥拉回来了,村里人赶来帮忙的帮忙,庆贺的庆贺,叔叔伯伯哥哥们帮忙卸货的吆喝声,婶子大娘端茶递水的逗笑声,我们几个骄傲又掩饰不住的欢声笑语,在整个院子上空飘荡。要知道,那时候,全村还有好多家连瓦房都没有住上呢,我们要住进城里人一样的平房,这可比过年的时候穿身新衣服自豪要多了!
农村人三件大事:盖房子,娶媳妇,生孩子。盖房子是第一件大事,秋收秋种一过,农人们都得闲了,父亲庞大的建房工程在一串长长的鞭炮声中,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地开启了。为了省钱,其实是没有多余的钱,父亲邀请会盖房子的叔伯们,不会盖房子的堂兄们也不甘落后,争先恐后跑来和灰搬砖,母亲和大娘婶子们负责烧水做饭。整个院子里热闹非凡:小工们送泥灰送砖的来回穿梭的身影,叔伯们要求上料的吆喝声,婶子大娘们爽朗的笑声、饭菜的香味、蒸笼的水蒸气热气腾腾的从厨房里飘出来。我们比过大年还要兴奋,一会儿去运砖,一会儿去洗菜,生怕自己没有为新房増砖添瓦。
忙忙碌碌近一个月,新房的主体工程已经扫尾,剩下的零碎活就需要花费些时日精雕细琢,一顿丰盛的酒宴款待后,亲戚们都打着饱嗝,晃晃悠悠的回去了。父亲一个人蹲在院子里,点了支烟,静默着,只有烟头的火光在黑暗里一明一暗。一切都静下来了,静得能听到父亲粗重的呼吸,在黑暗里一起一伏。
累得脱了形的父亲该是很满足了吧:房子建得很高,比院子高出七个台阶,很巍峨的冠压四周。四间带走廊的阔大平房,完全是按照城里房子的设计,房间很大,可以摆上他女儿们要求已久的时髦的梳妆台,每个屋子不再用门帘而是装上了门,儿女们从此都有了自己的小天地。
父亲若生在富贵之家,一定是李白一样的浪漫主义诗人。这一点从他盖好房子后的细节雕琢上,就令我至今仍钦佩不已。院墙砌起来了,墙头上种上了易活的仙人掌,不两年就有嫩黄的花儿墙头绽放它的娇艳,院子里种上了各色月季,菊花等农村不大搭理的花花草草,搭上了两排葡萄架,我们可以在葡萄架下悠然穿行,桃树,杏树,梨树,柿子树,苹果树,连农村不常见到的桂花树,都在我们的院落里安了家。院落外面,则种上了清雅幽幽的竹子和风情万种的银杏。季季品瓜果,时时飘花香,清光门外一渠水,秋色墙头数点山。俨然一个活色生香的花果园,哪里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的院子,分明是高人雅士的隐居之所啊!
我们的家却偏偏不是隐居的所在,每到晚上,忙完农活,左邻右舍乃至东西村子里的叔伯们都会聚拢到我们家宽敞的堂屋里,听性格开朗见多识广的父亲高谈阔论。国家大事,新闻动态,当了多年村干部的父亲张口就来,头头是道;邻里纠纷,婆媳不睦,父亲三言两语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握手言欢。开轩面场,桑麻菽麦,父亲总是站在引领村里农业科技的最前沿。母亲则静静的在堂屋的角落里做她永远也做不完的针线活,时而抬头望望茶壶,看需不需要续上开水。宁谧的村庄上空,不时从我们家飘出一阵阵谈笑声。
春去秋来,我们这群乳燕一个个扑棱棱飞向了远方,每个露珠浸润的拂晓,听不见父亲发动拖拉机驶出院子的突突声;看不到父亲炎炎酷暑晌午干活归来的疲惫的倦容;每个树梢模糊的黄昏,听不到母亲站在台阶前手拈粮食轻唤喂鸡的咕咕声;看不到母亲月上柳梢头,戴月荷锄归,一边擀面条一边柔声啍唱小曲儿的背影。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渐渐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城打工,村子里只剩下老人与孩子,村子空了。最初是家里的喧闹声低落了,接着牲畜也稀疏了,早上听不到此起彼伏的公鸡打鸣,晚上听不到村落深处的东犬西吠。村子静下来了,父母老了,村子里的父辈们也老了,屋子也和他们一样,一天天的颓败了。
一年又一年,我们在这座房子里,送走了母亲,又送走了父亲,屋子空了。虽还和风霜雨雪鏖战,可已经没了生气,渐渐的,荒草爬满了老屋院子的各个角落。
老屋,怕要和这无数个村庄一样,载着父辈的旗帜和辉煌,载着我们年少的记忆,隐进岁月的深处了……
作者:韵岚
公众号:红罗山书院
本文为原创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