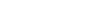海外学子的中国梦:青春同梦想一同飞翔
时间:
若木1由 分享
在外求知的莘莘学子,从未忘记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和光荣使命,为此他们没有停止思索——如何把自己所学的本领同祖国联系起来,如何让自己的青春挥洒得熠熠生光。他们是好样的,因为他们正在实现理想的征程中踏实前行
美国威廉玛丽学院博士王雪莹——
脚踏实地,理想激荡我心
2003年非典肆虐之时,我正读高中二年级,正在准备参加全国高中生生物学联赛。在我的记忆里,白色口罩几乎一夜之间成为“时尚”,板蓝根脱销,白醋告罄。每天都有新增病例,每天都有疑似病人被隔离,每天都有人死去,每天又有人冲进战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所有的人都显得义无反顾。
那些日子里,我每天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准时收看一天4次的新闻联播。新闻里,那些医务工作者冲上去、倒下、再次冲上去,顽强地站在抗击病魔的第一线。电视屏幕上闪过在救护过程中牺牲的医生、护士、科研人员的最后面容,令我泪流满面,却内心激越。两千年前,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用一场大火拯救了雅典;两千年后,中国的医护人员,用自己的勇气和生命挽救了瘟疫中的国家和人民。我第一次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像那些牺牲的白衣英雄们一样,用智慧和果敢去拯救危机中的生命和文明。正是因为心中怀着如此厚重的责任感,我选择了在高中毕业时被保送到华中科技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大学的生活自由丰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年轻的我,面对着这个鲜活而嘈杂的世界,内心充斥着欲望和野心,渐渐地忘却了当年的理想与使命。直到大二的一个暑假,一次刻骨铭心的社会实践考察,终于把我那被繁华现实所迷惑的心唤醒,让我重新找到了年少时那份最初的感动和执着。
2006年的7月,我带领华中科技大学生命学院的一个社会实践小队,进入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的艾滋病高发村落,展开对艾滋病人及其家庭生活现状的纪实采访。我们进驻的村庄是病情较为严重的地区,由中国政府和红十字会重点监护。我们被安排在“阳光家园”(建“阳光家园”,是为了帮扶一些艾滋家庭遗留的孤儿和老人,由专门的看护人员照顾他们的衣食住行)入住,每天走街串巷,与村民交谈,有选择地对部分家庭深入采访,了解他们的真实生活面貌。我多次被那些质朴的村民所感动,他们的乐观、坚韧和豁达,都深深地在我心上打下烙印。
至今令我记忆犹新的一个场景,是一天下午采访结束之后,村里的一群孩子簇拥着“护送”我们回驻地。黄昏时的村庄无比静谧,绿油油的一望无际的田地,连绵起伏的远处的山峦,在夕阳金色余晖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美丽。在这样宁静祥和的氛围下,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舒适惬意,却又无以复加的悲伤。孩子们在乡间的小路上嬉戏追逐,玩耍打闹,纵情地奔跑,放肆地高喊。一瞬间,这一切让我想起了自己遥远的童年和彼时无拘无束的快乐生活,然而眼前的这些孩子们,却在承受着我所无法理解的生活重负。
看到孩子们准备赛跑,我突然心血来潮地加入,并鼓励他们说,跑得快就有奖品。于是一声令下,孩子们个个像离弦的箭一样飞奔起来,我的心情也随之轻快地像要飞起来一样。我看见那个最小个头的小女孩被同伴们远远地甩在身后,生病导致的身体虚弱让她不停地喘着粗气,却仍然一副决不放弃的神态。我动容之下,跑过去一把将她抱在怀里,然后朝她的同伴们飞快地追上去。被追上的孩子都大声抗议说她在耍赖,她却在我的怀里乐开了花,扬着一张天真无邪的小脸咯咯地笑个不停。那一刻,我抱着她,就像抱着全世界最珍贵的一条小生命。我看着她笑,看着看着自己却笑出了泪花。
我曾对许多家人、朋友说,这样的一次社会实践,大概是我大学里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许多年后,我驾车行驶在异国他乡深夜空旷的高速公路上,脑海里依然清晰地浮现出那些孩子的脸庞,他们纯真的笑容,固执的护送,争先恐后地对我举手保证说一定要努力考上大学、走出村庄看看外面世界的幼稚承诺。我始终记得,那个夏天,我遇见那样一群人,他们让我看到了对生命最深重的敬仰与渴望,他们教会了我如何努力严肃地面对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所祈求的,只是一次好好生活的机会。
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历史悠久的威廉玛丽学院攻读神经生物学博士。赴美求学的这些年里,我有幸遇见良师益友,结识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他们每个人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和对全人类的悲悯,无不感染和鼓励着我。是的,我想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许多时候,想起2003年的非典,想起艾滋病村的孩子们,想起2008年的汶川地震,心里那份激越依然在胸怀荡漾。祖国所经历的每一次灾难和不幸,都会重重地敲打我的心。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仅仅是对着外国友人自豪地说一句“I’m proud of being Chinese”(“我为是中国人而自豪”),更是应该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身先士卒顶上去,说一声“交给我吧,请放心”。如果说我有一个中国梦,那么我想,这个梦想,无关名利,无关荣耀,只不过将来可以有一个机会,能让我安放那些年里所有的青春理想。
(本报记者张旸采访整理)
美国威廉玛丽学院博士王雪莹——
脚踏实地,理想激荡我心
2003年非典肆虐之时,我正读高中二年级,正在准备参加全国高中生生物学联赛。在我的记忆里,白色口罩几乎一夜之间成为“时尚”,板蓝根脱销,白醋告罄。每天都有新增病例,每天都有疑似病人被隔离,每天都有人死去,每天又有人冲进战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所有的人都显得义无反顾。
那些日子里,我每天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准时收看一天4次的新闻联播。新闻里,那些医务工作者冲上去、倒下、再次冲上去,顽强地站在抗击病魔的第一线。电视屏幕上闪过在救护过程中牺牲的医生、护士、科研人员的最后面容,令我泪流满面,却内心激越。两千年前,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用一场大火拯救了雅典;两千年后,中国的医护人员,用自己的勇气和生命挽救了瘟疫中的国家和人民。我第一次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像那些牺牲的白衣英雄们一样,用智慧和果敢去拯救危机中的生命和文明。正是因为心中怀着如此厚重的责任感,我选择了在高中毕业时被保送到华中科技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大学的生活自由丰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年轻的我,面对着这个鲜活而嘈杂的世界,内心充斥着欲望和野心,渐渐地忘却了当年的理想与使命。直到大二的一个暑假,一次刻骨铭心的社会实践考察,终于把我那被繁华现实所迷惑的心唤醒,让我重新找到了年少时那份最初的感动和执着。
2006年的7月,我带领华中科技大学生命学院的一个社会实践小队,进入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的艾滋病高发村落,展开对艾滋病人及其家庭生活现状的纪实采访。我们进驻的村庄是病情较为严重的地区,由中国政府和红十字会重点监护。我们被安排在“阳光家园”(建“阳光家园”,是为了帮扶一些艾滋家庭遗留的孤儿和老人,由专门的看护人员照顾他们的衣食住行)入住,每天走街串巷,与村民交谈,有选择地对部分家庭深入采访,了解他们的真实生活面貌。我多次被那些质朴的村民所感动,他们的乐观、坚韧和豁达,都深深地在我心上打下烙印。
至今令我记忆犹新的一个场景,是一天下午采访结束之后,村里的一群孩子簇拥着“护送”我们回驻地。黄昏时的村庄无比静谧,绿油油的一望无际的田地,连绵起伏的远处的山峦,在夕阳金色余晖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美丽。在这样宁静祥和的氛围下,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舒适惬意,却又无以复加的悲伤。孩子们在乡间的小路上嬉戏追逐,玩耍打闹,纵情地奔跑,放肆地高喊。一瞬间,这一切让我想起了自己遥远的童年和彼时无拘无束的快乐生活,然而眼前的这些孩子们,却在承受着我所无法理解的生活重负。
看到孩子们准备赛跑,我突然心血来潮地加入,并鼓励他们说,跑得快就有奖品。于是一声令下,孩子们个个像离弦的箭一样飞奔起来,我的心情也随之轻快地像要飞起来一样。我看见那个最小个头的小女孩被同伴们远远地甩在身后,生病导致的身体虚弱让她不停地喘着粗气,却仍然一副决不放弃的神态。我动容之下,跑过去一把将她抱在怀里,然后朝她的同伴们飞快地追上去。被追上的孩子都大声抗议说她在耍赖,她却在我的怀里乐开了花,扬着一张天真无邪的小脸咯咯地笑个不停。那一刻,我抱着她,就像抱着全世界最珍贵的一条小生命。我看着她笑,看着看着自己却笑出了泪花。
我曾对许多家人、朋友说,这样的一次社会实践,大概是我大学里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许多年后,我驾车行驶在异国他乡深夜空旷的高速公路上,脑海里依然清晰地浮现出那些孩子的脸庞,他们纯真的笑容,固执的护送,争先恐后地对我举手保证说一定要努力考上大学、走出村庄看看外面世界的幼稚承诺。我始终记得,那个夏天,我遇见那样一群人,他们让我看到了对生命最深重的敬仰与渴望,他们教会了我如何努力严肃地面对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所祈求的,只是一次好好生活的机会。
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历史悠久的威廉玛丽学院攻读神经生物学博士。赴美求学的这些年里,我有幸遇见良师益友,结识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他们每个人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和对全人类的悲悯,无不感染和鼓励着我。是的,我想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许多时候,想起2003年的非典,想起艾滋病村的孩子们,想起2008年的汶川地震,心里那份激越依然在胸怀荡漾。祖国所经历的每一次灾难和不幸,都会重重地敲打我的心。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仅仅是对着外国友人自豪地说一句“I’m proud of being Chinese”(“我为是中国人而自豪”),更是应该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身先士卒顶上去,说一声“交给我吧,请放心”。如果说我有一个中国梦,那么我想,这个梦想,无关名利,无关荣耀,只不过将来可以有一个机会,能让我安放那些年里所有的青春理想。
(本报记者张旸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