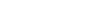刑事自诉的实践问题思考
时间:
张平1由 分享
【摘要】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审理的“先民后刑”实践模式,推动了恢复性、协商性司法理论的实践,当恢复性司法所彰显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效用为人们所接受后,在充分的理论准备、成熟的实践积累和长久的时间沉淀,刑事和解在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占有一席之地。与耗费国家司法资源来实现自己民事诉求的公诉案件不同,自诉案件需要自诉人以自己的资源来实现自己的民事诉求,除了非要让被告人定罪入刑以出口“恶气”外,自诉人选择刑事自诉通常是以刑事挤压民事来获得合理可观的民事赔偿。在个别自诉案件中,自诉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难以获得独立的救济空间,因为既然被告给予了足额的非精神损害赔偿,那么自诉人就应该撤诉,而自诉人撤诉却无法有效的弥补自己的损失和抑制被告的行为,不撤诉又难以保证民事赔偿的有效实现,并且招致法官的质疑和被告的愤恨,因此,对自诉案件能否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进行追问、分析和反思,有助于提升问题的认识能力和满足人们的合理诉求。自由裁量权是有效实现司法公正的“润滑剂”,没有自由裁量权的审判将难以保证个案的公正,而过分的自由裁量权也难以保护司法的公正,公诉案件中所涉及的自由裁量权更多表现在对犯罪嫌疑人刑罚轻重的问题,而自诉案件属于轻微的刑事案件,其所涉及的自由裁量权会表现在是否适用刑罚的问题,因此,法官在自诉案件审理中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更应当理性和公正的行使,而在乡村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审理自诉案件时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更会遭受司法外部运行环境的约束和司法有效回应社会诉求的压力。
【关键词】刑事自诉;实践属性;精神损害赔偿;自由裁量权;论文代写
【写作年份】2012年
【正文】
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和组成部分,代表国家依法行使审判权,它作出的裁判是基层人民法院的裁判。从诉权限制裁判权的司法理念和法院职能分工的制度安排来看,人民法庭审理民事案件(审理合同案件的范围有限)和刑事自诉案件,不审理行政案件,执行案件一般限于自己审结的案件,一审程序中不包括再审程序。笔者作为乡村人民法庭的工作人员,能够感受到得刑事司法实践只能是刑事自诉案件,法学研究要注重实践、面向基层和兼顾未来,对刑事自诉司法实践的观察、总结和反思能够使法学研究厚重化,因此,笔者将以遵循实证的和比较的研究进路,以内在性视角来研究乡村人民法庭的刑事自诉实践问题。
一、刑事自诉的实践属性思考
在乡村中,刑事自诉案件的数量很少而且诉因有限。对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而言,语言使用和人文环境阻碍了侮辱、诽谤行为的入罪,传统观念和地缘文化窒息了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行为和虐待行为的入罪,经济考量和理性选择放弃了侵占行为的入罪,而这些都与证据的保存和使用有关,与当事人付出的诉讼成本和法律收益不成比例有关,与注重社会效果和谐的结果导向有关,在这里法律需要与当地的风俗习惯在保持一定张力的前提下进行有效互动。
真正占刑事自诉主流的案件,为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伤的故意伤害案件。而这类案件必然伴随着附带民事诉讼,在实践中,这类案件往往先经过派出所或者当地村委会进行调解过滤,只有未满足被害人经济赔偿请求的轻伤案件才会诉至法院。因此,证据较为明确和充分,被害人选择刑事自诉往往可以对民事赔偿产生“神奇”的挤压效应,而令被害人满意的民事赔偿的实现可使犯罪嫌疑人换取一种“酌轻筹码”,以被害人的谅解来实现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减轻。[1]
自诉案件不比离婚案件,自诉人囿于自身法律素养、实践能力和操作技术等因素,自诉通常聘请诉讼代理人来弥补自身诉讼能力的不足。我国台湾地区规定了自诉的律师强制代理制度,同时,废除了当事人言词提前自诉的规定。根据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和司法运行环境,在乡村司法中,自诉人委托的代理人通常为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一般情况下,多数当事人委托法律工作者,其原因有二:一是法律工作者接近乡村司法需求服务市场,而自诉人也分不清国家规定分类经营的法律工作者和律师有什么区别;二是法律工作者的代理费用较律师低,大多自诉人只想利用刑事自诉来压迫民事赔偿,多数业务能力和实践技术强的法律工作者并不比一般律师能给其带来的收益低。而聘请律师为诉讼代理人的情况,无非是需要追求对被告人课以刑事责任,或者律师为了开发案源而鼓动自诉人请求法院对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在乡村法庭这种场域司法中,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在处理当事人纠纷上与审判人员、己方当事人和对方当事人及代理人的行为和效果是不相同的,通常接近法律服务市场的法律工作者对纠纷的有效解决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在一起故意伤害罪的自诉案中,当事人就聘请了一位市区里法律工作者,所写自诉状的格式都不正确。当法庭告知其证据不完善时,法律工作者说我们写撤诉申请,自诉的目的在于获得足额的民事赔偿。原告仅因被告用割猪草的镰刀一刀致使其左前臂严重刀砍伤和左手指伸肌腱血管断裂,就主张了医疗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等11项共计四万余元的赔偿主张,可见自诉人聘请法律工作者是为了实现被告人赔偿利益的最大化,也是为了降低向被告索赔的沉淀成本。由此可见,在乡村中,这类案件的实践逻辑是:没有当事人的民事赔偿诉求就没有当事人的刑事自诉。而刑事自诉是否对当事人具有实践效用就在于刑事自诉是否能够使民事赔偿得以挤压成功,从而起到强力校正的积极作用,从这个角度看,刑事自诉实则是当事人发生民事纠纷后对争议处理方式的理性考量和可行选择。
“侵权”同“犯罪”、“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界限是制度变迁的结果,而不应该遵循教条的意识形态使之区分成为永恒不变的真理。[2]在受害人通过刑事自诉来挤压民事赔偿的实践表象背后,隐藏着刑法的谦抑性的理论基础。刑法的谦抑性,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措施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刑法进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从单纯的惩罚到预防的犯罪,而且,预防观念本身也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从单纯依靠刑罚预防到采用多种措施进行社会预防。[3]在被告人能够合理的满足自诉人的民事赔偿诉求时,自诉人可以通过行使撤诉的权利来被告人免受刑事讼累。一般而言,金钱的失去比名誉的降低和自由的丧失对乡村人民更严重,而对于富人而言,名誉的贬损和自由的丧失比金钱的失去更严重,根据刑罚个别化的原理,对于被告人积极赔偿自诉的民事损失,是一种悔过的客观表现,既然自诉人和被告人泯去恩仇,刑罚就应当不能适用。同时,当被告的罪名成立,其所犯罪行轻微却要与公诉所确立的罪名接受同质的刑罚处罚方式,既不利于被告有效的回归社会,又不利于教育和感化被告。从自诉司法实践中,可以看出刑法的教义学应当吸收民法知识,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民法和刑法之间应当经历知识冲突、知识转换和知识整合的过程。根据社会学的田野调查研究,在以意识形态来划分阶级的阶级斗争时代,犯罪人难以回归社会,会被守法者带上有色眼镜来评价和教育;而以以经济实力来评价地位的经济建设时代,犯罪人回归社会有的成为乡村治理的“骨干”,以其狠劲来维护地域的稳定和发展村庄的经济。
综上所述,虽然法律规范将自诉定性为刑事属性,但文本的权威性表述并不能规范自诉的实践属性,自诉在很大程度上被自诉人用来实现自己争讼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其民事赔偿的获得才是自诉人的目的,因此,笔者认为自诉的实践属性是民事属性。在个别自诉案件中,自诉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难以获得独立的救济空间,因为既然被告给予了足额的非精神损害赔偿,那么自诉人就应该撤诉,而自诉人撤诉却无法有效的弥补自己的损失和抑制被告的行为。同时,为了有效节约和配置有限的司法资源,自诉人不得向对方请求支付代理费用,因此,自诉人很难通过诉讼使自己恢复到纠纷发生前的状态。放眼国外,美国高额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实践不但能够有效的救济被害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被告人的行为,刑罚也很少使用。因此,笔者下文将讨论自诉案件能否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二、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思考
传统刑事诉讼法理论,没有对被害人地位予以合理的考虑和科学的定位,抽象性的将国家和被害人对加害人的要求完全同一化,并按照国家的意志来实现对加害人的惩戒,刑事案件不能向被告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就是国家意志代表被害人意志的具体体现。然而,随着社会异质化、意志自主化和思想多元化,被害人和国家对加害人的期待和要求必然会有所差异,将这个众所周知的刑事司法实践常识再问题化,理论界也并没有对刑事案件能否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达成共识。王利明教授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受害人的抚慰和对加害人的制裁,其功能具有多重性。正是因为精神损害赔偿具有补偿性,所以在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中,也应当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5]
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审理中,附带民事诉讼的判决是以刑事诉讼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为依据的。与公诉案件的性质相比,自诉案件属于轻微的刑事案件,自诉人为了效仿刑事和解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理性地选择自诉来实现对民事赔偿产生挤压的效应,然而,公诉案件所侵害的抽象受害人国家通过检察部门来实现对犯罪嫌疑人的刑事惩罚和实现具体受害人的民事诉求,而自诉人只能通过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实现自己的诉求,可以说公诉案件被害人可以通过搭检察机关的“顺风车”来实现诉求,而自诉案件的受害人因案件性质轻微而只能自己“掏钱买票”来实现诉求。尽管公诉案件中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害大于自诉案件中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害,但国家出于规模经济和司法效率考虑为公诉案件配置司法资源,也应当给自诉案件提供相应的激励机制和合理方式来弥补自诉人“买票”的损失,因此,对于遭受精神损害的自诉人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是合理可行的。而且,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高低对刑罚的适用也有一定影响的,美国通过高额赔偿对违法毁损名誉行为发挥抑制机能,现在美国在名誉毁损中很少使用刑罚;日本由于赔偿额较低,所以不得不依赖刑罚抑制这种恶质的事例。[6]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2条规定,被侵权人只有在侵权人侵害其人身权益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才能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在自诉案件这种轻微的刑事案件中,自诉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程度是否能够满足严重这个限制条件而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笔者将写实性地简述一起离婚纠纷来分析这个问题。
法庭来了甲男、乙女、丙女三人。丙告诉法官她父亲甲和母亲乙来离婚的,甲同意和乙离婚,但甲出尔反尔,所以她和乙将甲拉来,本来她弟弟和弟媳也要来支持父母离婚的,她和弟弟是甲和乙亲生的,自己也有一个两岁的女儿。在法官感到惊讶后,得知:甲经常妄想乙和与乙说话的任何男性有性关系,甲不管场合的辱骂乙,其言语不堪入耳,儿女听不下去,邻居也看笑话,而甲精神正常,与其他人相处没有问题。
1、甲是否构成犯罪
本案中,甲捏造并散布乙与他人有婚外性行为的事实,该行为足以败坏乙的名誉并且具有多次实施诽谤行为的情节严重,根据我国《刑法》第246条的规定,乙并无婚外性行为的事实,但甲捏造并散布乙有婚外性行为的事实,情节严重的,构成诽谤罪。[7]但是,甲的行为并没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要想追究甲的刑事责任只能通过乙进行刑事自诉。
2、乙能否自诉
甲和乙系配偶关系,乙能否提起对甲的自诉。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321条规定,对于直系尊亲属或者配偶,不得提起自诉。陈朴生先生认为:对簿公堂,不特有伤固有道德,于社会善良风俗,亦非所宜。[8]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配偶间不得提起自诉,自诉作为一种权利只要法没有明文规定限制条件即可自由行使,况且,我国《刑法》所规定自诉案中的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和虐待案常常发生在配偶或者亲属关系之间,因此,此案甲和乙的夫妻关系并不影响乙提起对甲自诉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在日常生活中,男人骂女人“婊子”等捏造和散布她人有婚外性行为的场景并不少见,自诉通常不能成立,因为这受到语言使用环境、社会人文观念和传统地域文化的制约。
3、乙能否获得精神损害赔偿
我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了四种无过错方可以向导致离婚的过错方提出损害赔偿,此案中的乙能否对甲请求离婚损害赔偿,关键看如何定义和理解家庭暴力的内容。甲没有对乙实施形体暴力(硬暴力),但甲的诽谤行为对乙实施了语言暴力(软暴力),如果不能将语言暴力认定为家庭暴力,那么,乙能否依据《侵权责任法》第2条和第22条请求甲进行精神损害赔偿。甲的行为足以败坏乙的名誉,严重伤害了夫妻感情,从其子女的反应来看,乙遭受了社会一般人都难以忍受和承受的精神痛苦,因此,笔者认为乙可以依据《侵权责任法》向甲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4、本例的意义所在
通过分析这个离婚纠纷,可以看出以刑事判决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也可能征表出自诉人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如果自诉案件不允许自诉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那么既体现出刑事司法制度对自诉安排的不合理,又体现出对加害人行为抑制和对被害人救济的有限性。而且,为了使更多的被侵权人能够得到精神损害赔偿,法官在掌握精神损害严重程度的时候,降低严重精神损害的标准和尺度,[9]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加害行为的抑制。
【关键词】刑事自诉;实践属性;精神损害赔偿;自由裁量权;论文代写
【写作年份】2012年
【正文】
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和组成部分,代表国家依法行使审判权,它作出的裁判是基层人民法院的裁判。从诉权限制裁判权的司法理念和法院职能分工的制度安排来看,人民法庭审理民事案件(审理合同案件的范围有限)和刑事自诉案件,不审理行政案件,执行案件一般限于自己审结的案件,一审程序中不包括再审程序。笔者作为乡村人民法庭的工作人员,能够感受到得刑事司法实践只能是刑事自诉案件,法学研究要注重实践、面向基层和兼顾未来,对刑事自诉司法实践的观察、总结和反思能够使法学研究厚重化,因此,笔者将以遵循实证的和比较的研究进路,以内在性视角来研究乡村人民法庭的刑事自诉实践问题。
一、刑事自诉的实践属性思考
在乡村中,刑事自诉案件的数量很少而且诉因有限。对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而言,语言使用和人文环境阻碍了侮辱、诽谤行为的入罪,传统观念和地缘文化窒息了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行为和虐待行为的入罪,经济考量和理性选择放弃了侵占行为的入罪,而这些都与证据的保存和使用有关,与当事人付出的诉讼成本和法律收益不成比例有关,与注重社会效果和谐的结果导向有关,在这里法律需要与当地的风俗习惯在保持一定张力的前提下进行有效互动。
真正占刑事自诉主流的案件,为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伤的故意伤害案件。而这类案件必然伴随着附带民事诉讼,在实践中,这类案件往往先经过派出所或者当地村委会进行调解过滤,只有未满足被害人经济赔偿请求的轻伤案件才会诉至法院。因此,证据较为明确和充分,被害人选择刑事自诉往往可以对民事赔偿产生“神奇”的挤压效应,而令被害人满意的民事赔偿的实现可使犯罪嫌疑人换取一种“酌轻筹码”,以被害人的谅解来实现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减轻。[1]
自诉案件不比离婚案件,自诉人囿于自身法律素养、实践能力和操作技术等因素,自诉通常聘请诉讼代理人来弥补自身诉讼能力的不足。我国台湾地区规定了自诉的律师强制代理制度,同时,废除了当事人言词提前自诉的规定。根据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和司法运行环境,在乡村司法中,自诉人委托的代理人通常为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一般情况下,多数当事人委托法律工作者,其原因有二:一是法律工作者接近乡村司法需求服务市场,而自诉人也分不清国家规定分类经营的法律工作者和律师有什么区别;二是法律工作者的代理费用较律师低,大多自诉人只想利用刑事自诉来压迫民事赔偿,多数业务能力和实践技术强的法律工作者并不比一般律师能给其带来的收益低。而聘请律师为诉讼代理人的情况,无非是需要追求对被告人课以刑事责任,或者律师为了开发案源而鼓动自诉人请求法院对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在乡村法庭这种场域司法中,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在处理当事人纠纷上与审判人员、己方当事人和对方当事人及代理人的行为和效果是不相同的,通常接近法律服务市场的法律工作者对纠纷的有效解决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在一起故意伤害罪的自诉案中,当事人就聘请了一位市区里法律工作者,所写自诉状的格式都不正确。当法庭告知其证据不完善时,法律工作者说我们写撤诉申请,自诉的目的在于获得足额的民事赔偿。原告仅因被告用割猪草的镰刀一刀致使其左前臂严重刀砍伤和左手指伸肌腱血管断裂,就主张了医疗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等11项共计四万余元的赔偿主张,可见自诉人聘请法律工作者是为了实现被告人赔偿利益的最大化,也是为了降低向被告索赔的沉淀成本。由此可见,在乡村中,这类案件的实践逻辑是:没有当事人的民事赔偿诉求就没有当事人的刑事自诉。而刑事自诉是否对当事人具有实践效用就在于刑事自诉是否能够使民事赔偿得以挤压成功,从而起到强力校正的积极作用,从这个角度看,刑事自诉实则是当事人发生民事纠纷后对争议处理方式的理性考量和可行选择。
“侵权”同“犯罪”、“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界限是制度变迁的结果,而不应该遵循教条的意识形态使之区分成为永恒不变的真理。[2]在受害人通过刑事自诉来挤压民事赔偿的实践表象背后,隐藏着刑法的谦抑性的理论基础。刑法的谦抑性,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措施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刑法进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从单纯的惩罚到预防的犯罪,而且,预防观念本身也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从单纯依靠刑罚预防到采用多种措施进行社会预防。[3]在被告人能够合理的满足自诉人的民事赔偿诉求时,自诉人可以通过行使撤诉的权利来被告人免受刑事讼累。一般而言,金钱的失去比名誉的降低和自由的丧失对乡村人民更严重,而对于富人而言,名誉的贬损和自由的丧失比金钱的失去更严重,根据刑罚个别化的原理,对于被告人积极赔偿自诉的民事损失,是一种悔过的客观表现,既然自诉人和被告人泯去恩仇,刑罚就应当不能适用。同时,当被告的罪名成立,其所犯罪行轻微却要与公诉所确立的罪名接受同质的刑罚处罚方式,既不利于被告有效的回归社会,又不利于教育和感化被告。从自诉司法实践中,可以看出刑法的教义学应当吸收民法知识,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民法和刑法之间应当经历知识冲突、知识转换和知识整合的过程。根据社会学的田野调查研究,在以意识形态来划分阶级的阶级斗争时代,犯罪人难以回归社会,会被守法者带上有色眼镜来评价和教育;而以以经济实力来评价地位的经济建设时代,犯罪人回归社会有的成为乡村治理的“骨干”,以其狠劲来维护地域的稳定和发展村庄的经济。
综上所述,虽然法律规范将自诉定性为刑事属性,但文本的权威性表述并不能规范自诉的实践属性,自诉在很大程度上被自诉人用来实现自己争讼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其民事赔偿的获得才是自诉人的目的,因此,笔者认为自诉的实践属性是民事属性。在个别自诉案件中,自诉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难以获得独立的救济空间,因为既然被告给予了足额的非精神损害赔偿,那么自诉人就应该撤诉,而自诉人撤诉却无法有效的弥补自己的损失和抑制被告的行为。同时,为了有效节约和配置有限的司法资源,自诉人不得向对方请求支付代理费用,因此,自诉人很难通过诉讼使自己恢复到纠纷发生前的状态。放眼国外,美国高额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实践不但能够有效的救济被害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被告人的行为,刑罚也很少使用。因此,笔者下文将讨论自诉案件能否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二、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思考
传统刑事诉讼法理论,没有对被害人地位予以合理的考虑和科学的定位,抽象性的将国家和被害人对加害人的要求完全同一化,并按照国家的意志来实现对加害人的惩戒,刑事案件不能向被告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就是国家意志代表被害人意志的具体体现。然而,随着社会异质化、意志自主化和思想多元化,被害人和国家对加害人的期待和要求必然会有所差异,将这个众所周知的刑事司法实践常识再问题化,理论界也并没有对刑事案件能否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达成共识。王利明教授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受害人的抚慰和对加害人的制裁,其功能具有多重性。正是因为精神损害赔偿具有补偿性,所以在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中,也应当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5]
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审理中,附带民事诉讼的判决是以刑事诉讼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为依据的。与公诉案件的性质相比,自诉案件属于轻微的刑事案件,自诉人为了效仿刑事和解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理性地选择自诉来实现对民事赔偿产生挤压的效应,然而,公诉案件所侵害的抽象受害人国家通过检察部门来实现对犯罪嫌疑人的刑事惩罚和实现具体受害人的民事诉求,而自诉人只能通过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实现自己的诉求,可以说公诉案件被害人可以通过搭检察机关的“顺风车”来实现诉求,而自诉案件的受害人因案件性质轻微而只能自己“掏钱买票”来实现诉求。尽管公诉案件中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害大于自诉案件中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害,但国家出于规模经济和司法效率考虑为公诉案件配置司法资源,也应当给自诉案件提供相应的激励机制和合理方式来弥补自诉人“买票”的损失,因此,对于遭受精神损害的自诉人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是合理可行的。而且,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高低对刑罚的适用也有一定影响的,美国通过高额赔偿对违法毁损名誉行为发挥抑制机能,现在美国在名誉毁损中很少使用刑罚;日本由于赔偿额较低,所以不得不依赖刑罚抑制这种恶质的事例。[6]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2条规定,被侵权人只有在侵权人侵害其人身权益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才能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在自诉案件这种轻微的刑事案件中,自诉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程度是否能够满足严重这个限制条件而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笔者将写实性地简述一起离婚纠纷来分析这个问题。
法庭来了甲男、乙女、丙女三人。丙告诉法官她父亲甲和母亲乙来离婚的,甲同意和乙离婚,但甲出尔反尔,所以她和乙将甲拉来,本来她弟弟和弟媳也要来支持父母离婚的,她和弟弟是甲和乙亲生的,自己也有一个两岁的女儿。在法官感到惊讶后,得知:甲经常妄想乙和与乙说话的任何男性有性关系,甲不管场合的辱骂乙,其言语不堪入耳,儿女听不下去,邻居也看笑话,而甲精神正常,与其他人相处没有问题。
1、甲是否构成犯罪
本案中,甲捏造并散布乙与他人有婚外性行为的事实,该行为足以败坏乙的名誉并且具有多次实施诽谤行为的情节严重,根据我国《刑法》第246条的规定,乙并无婚外性行为的事实,但甲捏造并散布乙有婚外性行为的事实,情节严重的,构成诽谤罪。[7]但是,甲的行为并没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要想追究甲的刑事责任只能通过乙进行刑事自诉。
2、乙能否自诉
甲和乙系配偶关系,乙能否提起对甲的自诉。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321条规定,对于直系尊亲属或者配偶,不得提起自诉。陈朴生先生认为:对簿公堂,不特有伤固有道德,于社会善良风俗,亦非所宜。[8]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配偶间不得提起自诉,自诉作为一种权利只要法没有明文规定限制条件即可自由行使,况且,我国《刑法》所规定自诉案中的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和虐待案常常发生在配偶或者亲属关系之间,因此,此案甲和乙的夫妻关系并不影响乙提起对甲自诉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在日常生活中,男人骂女人“婊子”等捏造和散布她人有婚外性行为的场景并不少见,自诉通常不能成立,因为这受到语言使用环境、社会人文观念和传统地域文化的制约。
3、乙能否获得精神损害赔偿
我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了四种无过错方可以向导致离婚的过错方提出损害赔偿,此案中的乙能否对甲请求离婚损害赔偿,关键看如何定义和理解家庭暴力的内容。甲没有对乙实施形体暴力(硬暴力),但甲的诽谤行为对乙实施了语言暴力(软暴力),如果不能将语言暴力认定为家庭暴力,那么,乙能否依据《侵权责任法》第2条和第22条请求甲进行精神损害赔偿。甲的行为足以败坏乙的名誉,严重伤害了夫妻感情,从其子女的反应来看,乙遭受了社会一般人都难以忍受和承受的精神痛苦,因此,笔者认为乙可以依据《侵权责任法》向甲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4、本例的意义所在
通过分析这个离婚纠纷,可以看出以刑事判决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也可能征表出自诉人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如果自诉案件不允许自诉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那么既体现出刑事司法制度对自诉安排的不合理,又体现出对加害人行为抑制和对被害人救济的有限性。而且,为了使更多的被侵权人能够得到精神损害赔偿,法官在掌握精神损害严重程度的时候,降低严重精神损害的标准和尺度,[9]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加害行为的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