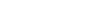重回公共利益:“三网融合”的价值重置可能
时间:
胡正荣 姬德强 1由 分享
关键词: 公共利益 三网融合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转向过程中,电信、广电以及之后的“三网融合”扮演了关键角色。以信息科技为特征的传播不仅自成产业,而且成为重组现代社会结构的核心机制。在此意义上,有关“三网融合”公共政策的制定,就超越了部门利益的窠臼,对和谐社会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在考察“三网融合”的历史发展、发生背景及现实进程的基础上,对其政策走向的价值重置进行重审,以期寻找其他的可能路径。
广电与电信遭遇增长“瓶颈”
从1999年国办发82号文禁止广电与电信的双向进入,到2010年1月国务院对“三网融合”开始实质性推进,产业政策发生了变迁。与此相伴的是广电与电信的“拉锯战”,一系列的“领土纷争”则起始于两者遭遇的增长瓶颈。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传统上相对隔离的广电和通信产业面临市场容量日趋饱和的窘境。一方面,如学者黄升民所言,广电面临着“深刻的经营危机”,而“电信在主营业务不断下滑的同时,还要面对投入巨大成本建立的3G业务和实施的宽带改造至今并未展现商业回报的问题”。另一方面,两个部门的市场化推进开始触及传统上作为“界标”的对方领地,如互联网服务、IPTV内容生产等。
在此前提下,一系列的增长“瓶颈”呼吁破除政策的坚冰和既有的利益空间,将“市场化”和“商品化”的范围和规模加以拓展。如此,“三网融合”成为解决各方积累和扩张问题的重要手段。在强调这一变革进程的市场主导角色的同时,政策层面的“坚冰”亦受到“放松管制”思潮的挑战。
“三网融合”≈信息化?
在政治经济学框架中,“三网融合”是以“信息化”的重要构成要素被合法化的,早在20世纪90年代便进入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议程。如1997年召开的首届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对“信息化”和“国家信息化”进行了定义:“信息化是指培育、发展以智能化工具为代表的新的生产力并使之造福于社会的历史过程。国家信息化就是在国家统一规划和组织下,在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国防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深入开发广泛利用信息资源,加速实现国家现代化进程。”
在此意义上,对中国这一发展中国家来说,“信息化”意味着现代化的一个崭新阶段,即“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并借此确立自身在全球新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根据上述会议要求,“信息化”的实现需要一个六位一体的“国家信息化体系”,那就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建设国家信息网络,推进信息技术应用,发展信息技术和产业,培育信息化人才,制定和完善信息化政策”。
由此,中国的“信息化”被定义为一个涉及政策修订,关联社会多个行业和部门,以信息科技和信息逻辑加以重塑的社会生产结构的变革过程,而不仅仅指涉传统意义上的“媒介产业”。这是讨论“三网融合”在中国社会历史框架中的具体定位和功能的出发点。
因此,“信息化”——结合不断加深的“市场化”——就绝非简单的技术更新和产业更替,而是涉及社会政治经济的重构和阶层变迁,以及更为重要的社会发展理念和价值的“自然化”趋势。
作为调节者的国家政策
尽管广电与电信各自的融合需求已经显而易见,“为谁融合、如何融合”仍然是国家政策在考虑“三网融合”发展方向上的前设性问题。换句话说,广电与电信的利益博弈不是也不应成为“三网融合”的全部内容。
一方面,国家意志选择推行“三网融合”,应主要考虑国民经济信息化趋势与全球经济发展的结构性转向,尤其是中国日益融入全球数字经济进程的现实加速了这一本土经济结构的转换进程。广电和电信的“内耗”将在宏观层面影响国民经济的增长。
另一方面,国家政策不仅考虑经济发展,还涉及政治制度和社会建设。不管是国家信息化,还是基于“单一现代性”的民族主义的“赶超”逻辑,都无法摆脱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换句话说,国家信息化的趋势已经确立,但如何建构符合并平衡各种参与者利益的政治经济制度,才是政策制定的关键问题。
“三网融合”的价值重置
既然现实的“三网融合”进程伴随着结构性偏见,价值重置就需跳出这一逻辑,回归或者想象新的路径选择。它应以对资本利益的批判为前提,以对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普通群众)的普遍服务为旨归,继承电信和广电传统的 “公共服务”职能,在最大程度上缩小城乡、阶层间的“信息鸿沟”,并进而参与一个更为公平、公正的社会结构的重建。
首先,“三网融合”的“公共服务”职能需要突出传播部门的普遍服务角色,而不仅仅聚焦于单纯的部门利益群体,从而使普通群众能够获得公平的参与机会。换而言之,“三网融合”需首先走出偏向精英群体利益和话语的阶层偏见,将最为普遍的大众作为服务和参与主体。
其次,反思和抵制资本化逻辑。通过引入上述“普遍服务”和“公共利益”的价值导向,平衡市场化与资本化的强大惯性,尤其需要重视社会主义广电和电信的历史遗产,并以此修正现代性意识形态框架,为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公共服务”为旨归的“三网融合”奠定认识论基础,进而以此“认识论转向”影响全球范围内的数字资本主义结构和趋势。
再次,实现“三网融合”的城乡平衡。“三网融合”不应致力于扩大广电和电信的市场规模,延伸二者资本化的触角至农村地区,并进而通过“剥夺式积累”加大城乡差距。相反,应将既有的城乡二元体制作为需要破除的歧视性社会结构,通过积极的乡村“三网融合”建设,将广电网络、电信网络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基础设施之一,在此基础上提高农村信息服务水平。简而言之,应从“三农”视角而不是城市的角度建设传播渠道和内容,从而实现真正的为农村服务。
最后,实现地域间的平衡。不管是广电还是电信,都已将经济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和中西部核心城市作为市场拓展的主要地理区域,从而使地域间的“信息鸿沟”日渐扩大。在“公共服务”的价值基点上,“三网融合”需要将自身重新定位为平衡地区间发展差异的重要驱动力。
可见,广电与电信的“公共服务”职能需要重新回到政策议题的中心。如此,“三网融合”才能够持续发展和壮大,并真正为人民群众提供精神文化服务,为持续深入的社会改革提供新的发展可能。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转向过程中,电信、广电以及之后的“三网融合”扮演了关键角色。以信息科技为特征的传播不仅自成产业,而且成为重组现代社会结构的核心机制。在此意义上,有关“三网融合”公共政策的制定,就超越了部门利益的窠臼,对和谐社会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在考察“三网融合”的历史发展、发生背景及现实进程的基础上,对其政策走向的价值重置进行重审,以期寻找其他的可能路径。
广电与电信遭遇增长“瓶颈”
从1999年国办发82号文禁止广电与电信的双向进入,到2010年1月国务院对“三网融合”开始实质性推进,产业政策发生了变迁。与此相伴的是广电与电信的“拉锯战”,一系列的“领土纷争”则起始于两者遭遇的增长瓶颈。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传统上相对隔离的广电和通信产业面临市场容量日趋饱和的窘境。一方面,如学者黄升民所言,广电面临着“深刻的经营危机”,而“电信在主营业务不断下滑的同时,还要面对投入巨大成本建立的3G业务和实施的宽带改造至今并未展现商业回报的问题”。另一方面,两个部门的市场化推进开始触及传统上作为“界标”的对方领地,如互联网服务、IPTV内容生产等。
在此前提下,一系列的增长“瓶颈”呼吁破除政策的坚冰和既有的利益空间,将“市场化”和“商品化”的范围和规模加以拓展。如此,“三网融合”成为解决各方积累和扩张问题的重要手段。在强调这一变革进程的市场主导角色的同时,政策层面的“坚冰”亦受到“放松管制”思潮的挑战。
“三网融合”≈信息化?
在政治经济学框架中,“三网融合”是以“信息化”的重要构成要素被合法化的,早在20世纪90年代便进入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议程。如1997年召开的首届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对“信息化”和“国家信息化”进行了定义:“信息化是指培育、发展以智能化工具为代表的新的生产力并使之造福于社会的历史过程。国家信息化就是在国家统一规划和组织下,在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国防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深入开发广泛利用信息资源,加速实现国家现代化进程。”
在此意义上,对中国这一发展中国家来说,“信息化”意味着现代化的一个崭新阶段,即“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并借此确立自身在全球新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根据上述会议要求,“信息化”的实现需要一个六位一体的“国家信息化体系”,那就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建设国家信息网络,推进信息技术应用,发展信息技术和产业,培育信息化人才,制定和完善信息化政策”。
由此,中国的“信息化”被定义为一个涉及政策修订,关联社会多个行业和部门,以信息科技和信息逻辑加以重塑的社会生产结构的变革过程,而不仅仅指涉传统意义上的“媒介产业”。这是讨论“三网融合”在中国社会历史框架中的具体定位和功能的出发点。
因此,“信息化”——结合不断加深的“市场化”——就绝非简单的技术更新和产业更替,而是涉及社会政治经济的重构和阶层变迁,以及更为重要的社会发展理念和价值的“自然化”趋势。
作为调节者的国家政策
尽管广电与电信各自的融合需求已经显而易见,“为谁融合、如何融合”仍然是国家政策在考虑“三网融合”发展方向上的前设性问题。换句话说,广电与电信的利益博弈不是也不应成为“三网融合”的全部内容。
一方面,国家意志选择推行“三网融合”,应主要考虑国民经济信息化趋势与全球经济发展的结构性转向,尤其是中国日益融入全球数字经济进程的现实加速了这一本土经济结构的转换进程。广电和电信的“内耗”将在宏观层面影响国民经济的增长。
另一方面,国家政策不仅考虑经济发展,还涉及政治制度和社会建设。不管是国家信息化,还是基于“单一现代性”的民族主义的“赶超”逻辑,都无法摆脱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换句话说,国家信息化的趋势已经确立,但如何建构符合并平衡各种参与者利益的政治经济制度,才是政策制定的关键问题。
“三网融合”的价值重置
既然现实的“三网融合”进程伴随着结构性偏见,价值重置就需跳出这一逻辑,回归或者想象新的路径选择。它应以对资本利益的批判为前提,以对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普通群众)的普遍服务为旨归,继承电信和广电传统的 “公共服务”职能,在最大程度上缩小城乡、阶层间的“信息鸿沟”,并进而参与一个更为公平、公正的社会结构的重建。
首先,“三网融合”的“公共服务”职能需要突出传播部门的普遍服务角色,而不仅仅聚焦于单纯的部门利益群体,从而使普通群众能够获得公平的参与机会。换而言之,“三网融合”需首先走出偏向精英群体利益和话语的阶层偏见,将最为普遍的大众作为服务和参与主体。
其次,反思和抵制资本化逻辑。通过引入上述“普遍服务”和“公共利益”的价值导向,平衡市场化与资本化的强大惯性,尤其需要重视社会主义广电和电信的历史遗产,并以此修正现代性意识形态框架,为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公共服务”为旨归的“三网融合”奠定认识论基础,进而以此“认识论转向”影响全球范围内的数字资本主义结构和趋势。
再次,实现“三网融合”的城乡平衡。“三网融合”不应致力于扩大广电和电信的市场规模,延伸二者资本化的触角至农村地区,并进而通过“剥夺式积累”加大城乡差距。相反,应将既有的城乡二元体制作为需要破除的歧视性社会结构,通过积极的乡村“三网融合”建设,将广电网络、电信网络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基础设施之一,在此基础上提高农村信息服务水平。简而言之,应从“三农”视角而不是城市的角度建设传播渠道和内容,从而实现真正的为农村服务。
最后,实现地域间的平衡。不管是广电还是电信,都已将经济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和中西部核心城市作为市场拓展的主要地理区域,从而使地域间的“信息鸿沟”日渐扩大。在“公共服务”的价值基点上,“三网融合”需要将自身重新定位为平衡地区间发展差异的重要驱动力。
可见,广电与电信的“公共服务”职能需要重新回到政策议题的中心。如此,“三网融合”才能够持续发展和壮大,并真正为人民群众提供精神文化服务,为持续深入的社会改革提供新的发展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