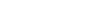全媒体战略:媒介改良的动因分析(2)
时间:
同心 吕强龙1由 分享
“全媒体”:改良策略的产生动因
作为中国互联网的风云人物之一,和讯网CEO谢文曾评价“全媒体”只是改良,而“新媒体”则是革命,其摧朽创新的深浅程度不可同日而语。尽管不断有人强调,全媒体流程再造的核心应是内容流程再造,不仅要提供一般意义上的“更多信息”,而且应该是“更多有效的异质信息”,输送“立体式”信息。然而,这也许并不能成为“全媒体”取胜的“王道”。“全媒体”战略的本意在彰显媒体、媒介的作用,无论如何,信息仍是经由编辑把关后选择性呈现的,与受众依然是不对称的交互。而“新媒体”,如微博、SNS最大的区别即在于它已经形成一种平台,而在淡化媒体中介的身份,实现用户间的交互,每个人都可以向其他人传播信息。而“全媒体”即使对记者进行全方位“武装”,单枪匹马与群众路线之实力悬殊似乎亦不证自明。
“碎片化”似乎是对新媒体传播特征的有效注解,也成为经由系统编码的传统媒体不屑的软肋。然而,传统媒体的线性文本强调内部结构,即意义的会聚性,抑或某种主题,传播信息是井然有序的,逻辑严明、完整,却已经经过中介把关人的筛选,呈现的是部分真实,也是遮蔽后的片段真实;而漫游于网络超文本中,每次探寻之外总是存在新的可能性,形成了无数“意指链”(a chain signification),山外有山、峰回路转,众声喧哗中,散落了各式信息,却于无意间更为接近本就无章的现实世界,新媒体呈现了真实,至少是真实的投影,有着非人工痕迹的完整面目。
上世纪西风东渐之时,士大夫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平衡各方利益进行有限改良。而现在的“全媒体”策略,也多少有这样传统媒介内容为主体,新媒介形态为外核的雷同。既然如上述分析,传统媒体为何不索性全面变革?
社会语境。历史学家陈旭麓曾经提出任何历史进程都有其惰性,即使它已不符合于时代,其完全变革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渐进消化。这似乎可以大而化之地解决疑问。当然,中国社会之复杂情状也可以作为重要的影响要素,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使得每一地区对于传播方式的要求以及能承受的传播成本都是有差异的。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报纸、广播仍然是这些地区受众的主要信息来源渠道。所以,传统媒体尚不急需全面改革,可以有更为稳妥的行进过程。然而,“全媒体”意在抢夺的是熟练使用网络新技术、并且有足够的时间资源和经济成本上网的用户——抑或是最具传播价值的中间阶层或准中间阶层。
商业谋求。商业利益的追逐可以成为第二层面的解释。“新媒体”即在于它已经形成一种平台,淡化媒体中介的身份,实现用户间交互,每个人都可以向其他人传播信息。也由于新媒体的传播特性,分流的受众可能是最受广告商青睐的一部分:或者是尚未形成完整、成熟观念的青少年,消费社会的潜移默化正为广告商培养潜在的消费者;或者是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中年人,而网络论坛社区形成的精准分类更为产品推广的有效投放提供了便捷的途径。“全媒体”与新媒体的根本差别,使得对于已习惯新媒体传播特征的人群而言,“全媒体”的吸引力可能有待商榷。
商业利益是推动传统媒体染指新媒体的现实助推力,但仍不能解释为何传统媒体不立即全面转变,尤其是对于系统编辑、管控的这一核心传播特征的守护。
文化领导权。麦克卢汉曾言:媒介即讯息,极言媒介本身的社会影响。的确,每一次媒介技术变革——印刷术、电子媒介、互联网,对时代的影响可谓深入肌理。近代中国的历程可以再次验证麦克卢汉的预言,各派学人几乎均选择以办报印刊的方式带领民众实现对现代性的追逐。而20世纪90年代电子媒介在中国大陆的兴起,促成了大众文化及消费社会的出现,成为当年最受瞩目的文化事件。可以说,传媒的确是一种新型的权力,不仅是指言说的话语权,更重要的是,在其传播过程中如若为民间认同,它也获得了“文化领导权”。葛兰西在《狱中札记》提出“文化领导权”或曰“文化霸权”理论,指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包括两方面,即“统治”(政治霸权)和“精神与道德的领导权”(文化领导权)。但这两方面也许并不能同步,在一个阶级控制着政治霸权时,文化领导权可能并不在它的手里。政治霸权和文化领导权的不同步,提出了一种历史可能性,即一个弱小的社会阶级可以依靠其文化优势,占据道德和文化的领导权,使革命获得道义性和合法性。
如上所述,新媒体有着诸多优势和传播的进步。然而,这种平台并非无偿交互。各类门户网站、博客播客、SNS等平台本就由商业资本搭建,利润仍是其追逐所向。网络以其巨大的公共空间和民间立场为饵,可以在此嬉笑怒骂,做足反抗主导文化的姿态;也可以只是剖白自己,发泄情绪或不满。然而在看似自由、发散、无序的网络世界中,不经意间点开的博客可能只是一篇品牌推广软文,而论坛最近时兴的话题可能只是由某个“枪手”打造,新加的SNS好友却不断推销产品,更不用说在每个页面旁边,都有与内容相关的商业广告——似乎有力量在监控受众所有的动向。在逃离了传统媒体的桎梏后,受众有可能陷入另一重迷雾,而网络世界的仿真程度更高。更加值得警惕的是,由于中国主流媒体的复杂责任与历史传统,受众似乎还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传统媒体所提供的消息尤其是负面的危机消息十分有限,而网络就成为各方“知情者”危机信息传播的渠道。并且,商业的渗透与危机信息的传播都很难视为单纯的经济利益驱动,某种意识形态正隐形地支配其中,建构所谓“人为的公共性”。
文化领导权并不是强制获得的,也不是变动不居的。所以,从新时代的文化领导权这一点出发,也许我们可以加深对传统媒体推出全媒体战略的了解:不可能完全放弃原有的媒介形态,更不可能弃用这种经由系统编辑的信息传播形式,即便是使用新媒体形态依然要沿用这一主动意识。全媒体战略的背后还有掌控、坚守和夺取的意味,这种有意识的舆论引导是不会消亡的命题。
注释:
①阿尔君·阿帕莱尔:《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见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23~524页。
参考文献:
1.罗鑫:《什么是“全媒体”》,《中国记者》,2010(3)。
2.新华社新闻研究所课题组:《中国传媒全媒体发展研究报告》,《科技传播》,2010(4),第8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