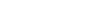揭示中国七种先富群体:政策致富是一般规律(12)
后富机制:跳出“带富”问题
无论在什么阶段,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过上相对体面而有尊严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可以作为共同富裕的价值体现或判断依据。
改革开放30多年了,如今富有群体的规模和财富积累是早期“先富者”难以望其项背的,“富二代”、贫富差距扩大等新的词汇或现象日益流行,就社会群体而言,经过代际转换,早已今非昔比。如果一定要在群体或阶层意义上讲“带”,还不如说富裕阶层如何帮助穷者脱贫或者变得富有,这恐怕是不可能的,因为太过道德伦理色彩。虽然我们看到不少富人行善,但这基本属于社会救济范畴,既不可能使穷人变富,也缺乏持续性机制。
因此,今天我们应该跳出群体或阶层意义上的“带富”问题,应该关注的是如何抑制或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并走向共同富裕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阶段,或者说我们已经没有“借口”拖延了。
首先是权力资本化问题。应该说,权力介入市场在计划经济体制引入市场调节机制的初期是不可避免的,没有这种介入,市场机制的自然生长是困难的。但权力本身也存在成为一种“资源”参与市场分配的可能,一旦条件成熟,这种可能就会变成现实。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利用产品“双轨”价差牟利,到90年代要素市场化中的“寻租”,人们不难观察到权力参与市场分配的演进轨迹。问题的实质在于,权力作为个人或群体的资源参与分配,本质上是对社会财富的瓜分,它在形成少数“暴富”阶层的同时,侵犯了他人创造社会财富的收益。
其次是劳工保护问题。一系列研究表明,我国劳动报酬率(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自1998年以来持续下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劳资之间的谈判机制,特别是工会力量还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再者是市场公平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资源根据市场需求自由进入或退出供给领域,这样才能实现公平竞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角度看,资源进出是否顺畅,直接对社会成员创业、就业、收入增长等一系列环节构成影响。
最后是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公共政策问题。我国是一个经过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旧体制的演变与新体制的形成与完善是一个不断“磨合”的过程,其间难免会出现所谓“越位”、“错位”、“缺位”现象,如行政性垄断、社会保障与福利、税赋轻重与公平等,这些方面的政策对收入分配格局也构成深刻影响。
共同富裕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或取向,不应该以国别来定义。这里的“共同”至少指社会绝大多数成员,至于什么样的水平标志富裕则与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这不应该有什么国别差异。我认为无论在什么阶段,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过上相对体面而有尊严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可以作为共同富裕的价值体现或判断依据。共同富裕不是指社会成员生活水平绝对无差别或拥有等量的财富,而是应该指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大体相当的富裕水平,相对差别在社会可接受范围。共同富裕也不是指在某一时点社会成员同时达到某种富裕水平,作为一种动态理念,它应包括致富机会的均等,即“时间可先后,机会要均等”。没有机会均等,恐怕不少人会长期处于“被平均”或“被富裕”的状态,收入与财富差距悬殊的现象难以改变。同时,机会平等也是社会保持活力与和谐、共同富裕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
至于共富的难题在哪,关键在于体制改革。体制不改革,好多政策不仅难以出台,而且执行起来也会发生扭曲。这是当前最大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