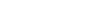民法中“民”的诠释(2)
时间:
赵玉 江游1由 分享
三、“民”体现了民法的方法
法律既然名之为法,就应该是一种方法,不同的法律部门应是不同的法律方法,能够解决不同法律问题的方法。民法亦然,民法就是一种特殊的方法,这种特殊的方法是由民法的 “民”所决定的,并集中表现在 “民”的方法上。
民法中的 “民”,有人认为 “智而强的人”,有人认为 “愚而弱的人”,还有人提出 “无色无味、面目模糊”的人。[9 ]民法中 “民”的形象决定着整个民法的属性,决定着民法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如果把民法的民想象为 “智而强的人”,把 “理性的”、 “审慎的”、 “机智的”、“精明的”、“认真的”、“恰当的”、 “勤勉的”等等,几乎把一切溢美之词都加在民法的 “人”身上,人难道真是这么完美无缺吗? 不是的,这种人只是极少数人,没有代表性,是一个拟制的人、甚至是虚假的人。如此设想人,就会排斥一大群,这种人只是社会少数精英,不宜叫之民,也许称之 “士”或 “贤”更准确,因为民总是包括、代表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按照这种“民”设计的民法就会成为 “智力产品”,甚至像哲学著作一样,只有少数 “智而强的人”才能理解和践行,而广大民众是无法知行的。这是一种高高在上脱离大众的 “士”法,是一种异化的民法。如果把民法的民想象为 “愚而弱的人”,那就贬低了一大群,他们成了特殊的民事主体,类似于被监护人、禁治产人之类的人,他们都不是能够完全意思自治的人,都是一些自己没有办法的人,按照这种 “民”设计的民法将异质于已有的民法,这是一种保姆式的法,保障式的法,很容易为国家干预和社会保障提供理由,同样会导致民法的异化,或民法的分化,如劳动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就是基于此而从民法中分离出来的。如果把人想象为 “无色无味、面目模糊的人”,如前所述,这种形象的人过于笼统、模糊,连基本、必要的区别如官与民的区别都抹杀了,导致官与民不分、政治社会与民间社会不分,这是不利于民法的存在和发展的,民法的民并非如此 “无色无味、面目模糊”,而是面目十分清晰,处处可见,比比皆是。总之,这三类民都不是民法的民,民法的民是 “常人”,是海德格尔所说的 “常人”,匈牙利数学家、统计学家凯特莱所谓的 “平均人”,是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那样的人,他们既不是 “智而强的人”,也不是 “愚而弱的人”,而是中等智力的人,一个普普通通的成年人。这是民法无论如何想方设法不能脱离的人,否则民法只能是屠龙之技,而不是安民之术。
“民”的界定决定了民法就是一套常言、常情、常识、常理和常规,它们是民众、民间的根本大法。民法要合乎这 “五常”,考量一个概念、原理、规则和制度是否为民法的概念、原理、规则和制度,最终标准就是视其是否合乎这 “五常”。民法是民用之法,要以能否为民所用为最高目标。这其实为民事立法、司法和民法研究指明了方向,民法要通俗易懂,要大众化、普及化,能为民所知行的法才是民法、良法。在这方面,法国民法典为立法者树立了榜样,它的语言一直受到后人的称赞,浅显易懂、生动明朗、文字优美,有人甚至说法国民法典是一部 “出色的法国文学著作”。这归功于拿破仑明确而坚定的立法思想,因为他希望这部法典能为全体法国人民读懂,法国人民能人手一册。实践证明,这一点差不多做到了。[10]但人们对民法 ( 包括其他法律) 有一种深刻的误解或强烈的偏见,那就是忘记、藐视这 “五常”。1896 年 《德国民法典》的制定,呈现出与 《法国民法典》不同的风格,这似乎给人们忘记、藐视这 “五常”提供了更加充分的理由。但这 “五常”是一切法学的基础和法理的根据,对于民法来说,认知了“五常”,就认知了民法,所以老子说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总之,“知常曰明”。有些人不深不休,其志可嘉,但不能为深而深,那些不必要的深是多余的,民法中的许多问题就是家长里短、日用常行、衣食住行,其中许多道理就像人要吃饭一样,简单明了,用不着 “深研细究”, “法深无善治”。况且,深入本身并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浅出”,深入深出不是好学问,甚至是伪学问,只有深入浅出才是好学问、真学问。真正的学问是穷极思辨但不离日用常行,如马克思主义就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但主要和基本的就是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盖棺论定地指出,虽然这是 “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但却是马克思的两大贡献之一。虽然马克思发现了这一 “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但后来我们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忘记了这一常识,以至于提出了 “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甚至 “停止生产闹革命”,导致祸国殃民。如老子所指出的“不知常、妄作凶”以及 “人弃常则妖兴”的古训,足以警示我们要用一种真正合乎民法精神、风格的态度和方式去对待民法和民法方法。
吉登斯指出,现代人生活在专家知识和抽象系统 ( abstract system) 里,[11]由于专门知识的垄断化以及抽象系统的大量存在,权力向专家学者转移,以至于专家学者的意见就是权威的意见,民众越来越信赖这种权威意见。随着民法的现代化,民法也变得越来越专业化、技术化、学术化或曰科学化,民法成了专家学者、甚至只是民法专家学者所垄断的知识,以 《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尤其如此,它向来被认为是 “法学家的法”。许多人认为民法是不断专业化、技术化的,如果说 《法国民法典》诞生于 “风车和磨坊”的时代, 《德国民法典》制定于 “声光电化”的时代,那么往后的民法更是徜徉在高科技之中了,民事生活的高科技化,必然要求民法的专业化、技术化。这里有一个专业化、技术化和学术化与民本化、大众化和通俗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它们之间应该能够很好地统一,并且是前者必须统一到后者,为后者服务,而不是相反。正像高端技术为了赢得市场必须 “傻瓜化”一样,民法为了赢得民众也必须民本化、大众化和通俗化,一切民法的专业化、技术化和学术化都应以此为依归。事实上,人们之所以需要专家学者把民法专业化、技术化和学术化,是为了使民法尽可能、更好地民本化、大众化和通俗化,而不是适得其反。只有当民法的准确性、严谨性和科学性无法兼顾民法的民本化、大众化和通俗化时,才不得不暂且如此,但一旦能够实现民法的民本化、大众化和通俗化时,还是应该以后者为重。况且,民法的民本化、大众化和通俗化也不一定会损害民法的专业化、技术化和学术化,相反只会使后者更能用得其所。由于广大民众不易甚至不能知行民法,于是只好花钱咨询专家、聘请律师,导致民法实务繁荣,催生各种牟利阶层。民法成了极少数人的专利,而不再为全体民众所日用,这实质上是民法的异化。诗尚可曲高和寡,但民法要服务民众,那种只有专家学者、高人乃至超人才能掌握和运用的东西,必然脱离民众和大众,没有社会基础,没有生命力,从根本上说是违反民法本质的。一些民法专家总想使民法 “超凡脱俗”,但民法的民众基础最终迫使民法 “与群众打成一片”,从根本上说民法不是由民法专家制定的而是由广大民众决定的,广大民众不能知行的民法不是真正的民法。后现代主义虽然有一定的反智意味,但这是对故弄玄虚的反感、反思和反弹,是返璞归真,删繁就简,去芜存精,是浮华过后的素朴。
民法的方法是民众的方法、通俗的方法、常识的方法,尊重民众的方法、民间的方法,民法本质上就是民众自主解决自己民事问题的方法,如民与民之间的契约即产生民事权利义务,所以民权不是来自于天赋、君授,而是来自于民创。这本是民法得以产生和存在的根基。一切反其道而行之的方法都不是民法的方法,如许多人对物权行为理论的批判即是如此。民法学者冯基尔克认为: “如果我们勉强的将单纯的动产让与分解为相对独立的三个现象时,的确会造成学说对实际生活的凌辱。到商店购买一副手套,当场付款取回标的者,今后也应当考虑到发生三件事情:其一,债权契约,基于契约发生当事人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 其二,与此债权契约完全分离的物权契约,纯为所有权的移转而缔结; 其三,交付的行为完全是人为拟制,实际上只不过是对于单一的法律行为有两个相异的观察方式而己。今捏造两种互为独立的契约,不仅会混乱现实的法律过程,实定法也因极端的形式思考而受到妨害。”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德国著名学者 Heek 也认为,普通公民在日常生活中,难以理解买卖行为中包括着三个行为,这有悖于国民的朴素感情。同时在立法上也是不经济的,因为民众不理解,需要培训法官、律师,导致立法方面的成本增长,故立法的不经济。[12]
四、“民”法比 “私”法更为精准
长期以来,民法又被称作私法,是私法的主体部分。但 “民”法比 “私”法更好,因为“私”法容易遭到人们的误解和反对,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以公有制为 ( 经济) 基础,曾经与私的东西不共戴天, “公而忘私”,也因为列宁那句话—— “我们不承认任何 ‘私人’性质的东西,在我们看来,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畴,而不是什么私人性质的东西。……对 ‘私法’关系更广泛地运用国家干预; 扩大国家废除 ‘私人’契约的权力; 不是把罗马法典,而是把我们的革命的法律意识运用到 ‘民事法律关系’上去。”[13]——而篡改民法,甚至否定民法,导致民法在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这都是由于 “名不正”而导致的 “言不顺”“理不通”和 “事不成”。但 “民”法并不会这样的,任何社会都有民,而且民还是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更是以民为本,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和主体,这与民法的属性原本是相通的。试想如果人民连民事都不能当家作主,怎么可能在政事( 治) 上当国 ( 政) 作主呢? 不经由民事的意思自治,怎么能有政事的民主自治呢? 民法与民主、特别是与社会主义的民主,在本质是高度一致的。
民法的 “民”并不是 “私人”,民法的权利也不是 “私权”,民法的利益也不是 “私利”。因为民法的民是社会中的民、社会化的民,不是孤立的个人、私人,其一举一动都与社会上其他人相关,都会影响到其他人,都处于社会关系网中,谁也无法 “私了”,所以民法也把自然人叫做 “公民”——民不再是私的了,已是公的了。这是十分准确的。民法是一套市场规则,民法的民是市场主体,是市民,他们必须参与社会分工,进行等价交换,无人能够自给自足、自私自利,谁自私自利,谁就自绝于民、自取灭亡。分工交易,互利互惠,这是市民必须遵循的社会公德,它对私人构成强有力的规训,使人不敢私而忘公。实践证明,越是市场化的市民越有社会公德,越不自私自利,越是合格的公民。民法的民是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民权是最广泛、最普遍的一种权利,人人享有,无民不享,是最具公共性的权利。当然,之所以把民权叫做私权,主要是因为它仅涉及私事。但自从社会化、特别是市场化以来,个人与社会、私事与公事已难以区分,私事与公事密切相关而且常常相互转化。如婚姻,虽是私人行为,但不到国家婚姻登记机关登记就不能受到民法的保护,许多人不是把真感情而是把结婚证视为婚姻的保护神,就说明了私的东西也需要公的确认、保护。民权虽说是私权,但民权的行使从来不可能私行,民权总是在社会中行使,在民众之间行使,如合同不仅有相对人,还有第三人。民权之间有互惠的一面,但也有冲突的一面,为此,权利不得滥用是民权行使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为私权注入了社会公德的要求。在现代社会,马克思所批判的那种 “脱离了人的本质和共同体的利己主义的权利”[14]的私权已经不复存在了,或者说在社会公德的规训和谴责下只能处于潜在状态。关于私权与公权、私法与公法的区分,已没有原初那么重要的意义了。民法是一套平等、自由、交互的利益准则,它保证人人平等自由地逐利,它要求人们等价互惠地获利。这种利已经发生了质变,一种有利人人、全民的利不是私利而是公利,甚至是真正的公利。一种能使人人逐利、获利的法律,一种能使利益互惠、利益均等、利益共赢的法律,不是私法而是公法,而且是最名副其实的公法。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去重新理解所谓的 “公法”和 “私法”。
五、民法中 “民”的发展
民法的 “民”相对于抽象的人来说,更为具体,但 “民”依然很笼统,还是不够具体; 民相对于官来说,刻意加以区分,但在民与民之间就不作进一步的区分了。民法典反映的人像,始终是无色无味,不笑不愠。这样的 “民”才能满足民法形式理性的要求。民法把千差万别的民抽象为平等的、自由的、同样的主体,民法看 “民”是只看是不是民,而不看是什么民。如果民法的民是 “无色无味、面目模糊的”。就不能体察民意和体恤民情了。如劳动者、消费者,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他们被认为是 “愚而弱的人”,对他们需要制定特别法予以倾斜保护,传统民法已包容不了它们,它们从一般民法中区分出来了。随着民法的 “民”在不断地分化、细化,与此相伴,还有一些法律将从民法中分立出来。
民法是一套市场法则,贯彻的是市场逻辑,民法的民是市民,是市场之中的民。那些不能进入市场领域、参与市场分工、进行市场交易、分享市场成果的人,就不是市民,就会被民法所无情地抛弃。既然民法的民是市民,就难免有某种市侩气,如利字当头,“利行私事”; 讨价还价,斤斤计较; “无因管理”所暗示的 “各人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以意思自治为名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等等,这些都与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不太协调。虽然民法的民不能毫不利人专门利己,但他们也不是道德楷模,人们没有理由期望他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民法的一个基本价值观念就是,世上没有救世主,人们只能自己救自己,民法只要求民独善其身,但不强求其兼济天下,民法并不博爱,它强烈地暗示着: 那些不能自救的民就只能自灭了。
民法是市场法则,自然也是竞争法则,将千差万别的 “民”置于同一规则下,任其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最终只有少数优胜者才能享有民法所规定的各种权利,这些权利蜕变为少数人的特权,而多数人无法问津。民法的平等、自由都是形式意义上的,不能保证实质意义上的平等、自由,民法是一套形式平等、自由但实质不平等、不自由的规则,它具有异化的本能。民法所崇尚的民必然地趋向 “智而强”,许多劣汰者将被驱逐于民法之外,失去民法之民的资格。民法将由全民之法走向少数精英之法。民法的民不能也不应仅仅是市民,更不能仅仅是极少数市场竞争的优胜者。民法的这种异化必须被归化,使民法回归为全民之法。
民法是利益的准则,民法中的民首先追逐的是自己的利益,虽然在平等互利、等价交换等原则的规范下,民在追逐自己利益的同时会受一只 “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会不知不觉地去促进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但从自己利益到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有相当多的环节和相当长的过程,使得两者并不能高度因应、完全一致,相反,两者常常存在冲突,此消彼长,并非共赢。如黑格尔认为: “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共同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15]所以,要促进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仅有民法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不同于民法之民的其他社会主体去推动,需要不同于民法制度的其他法律制度安排。民法不是万能的,不应该横行霸道,所谓 “民法帝国主义”是错误而有害的。
注释:
[1][德]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28 页。
[2][德]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46 页。
[3][古罗马] 查士丁尼: 《法学阶梯》,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第 12 页。
[4]周枏: 《罗马法原论 ( 上) 》,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97 页。
[5]《拿破仑法典》,李浩培、吴传颐、孔鸣岗译,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64 页。
[6][法]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 ( 下) 》,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68 页。
[7][英] 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73 页。
[8][美] 马勒: 《保守主义》,刘曙辉、张容南译,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36 页。
[9]谢鸿飞: 《现代民法中的 “人”: 观念与实践》,http: / /www. iolaw. org. cn/shownews. asp? id =435,2012 年3 月20日访问。
[10][德] 茨威格特、克茨: 《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66 页。
[11]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 - Identity :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31.
[12]孙宪忠: 《物权行为理论中的若干问题》,http: / /www. iolaw. org. cn/showscholar. asp? id = 79,2012 年 3 月 20 日访问。
[13]《列宁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27 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437 页。
[15] 同前引[2],黑格尔书,第 309 页。